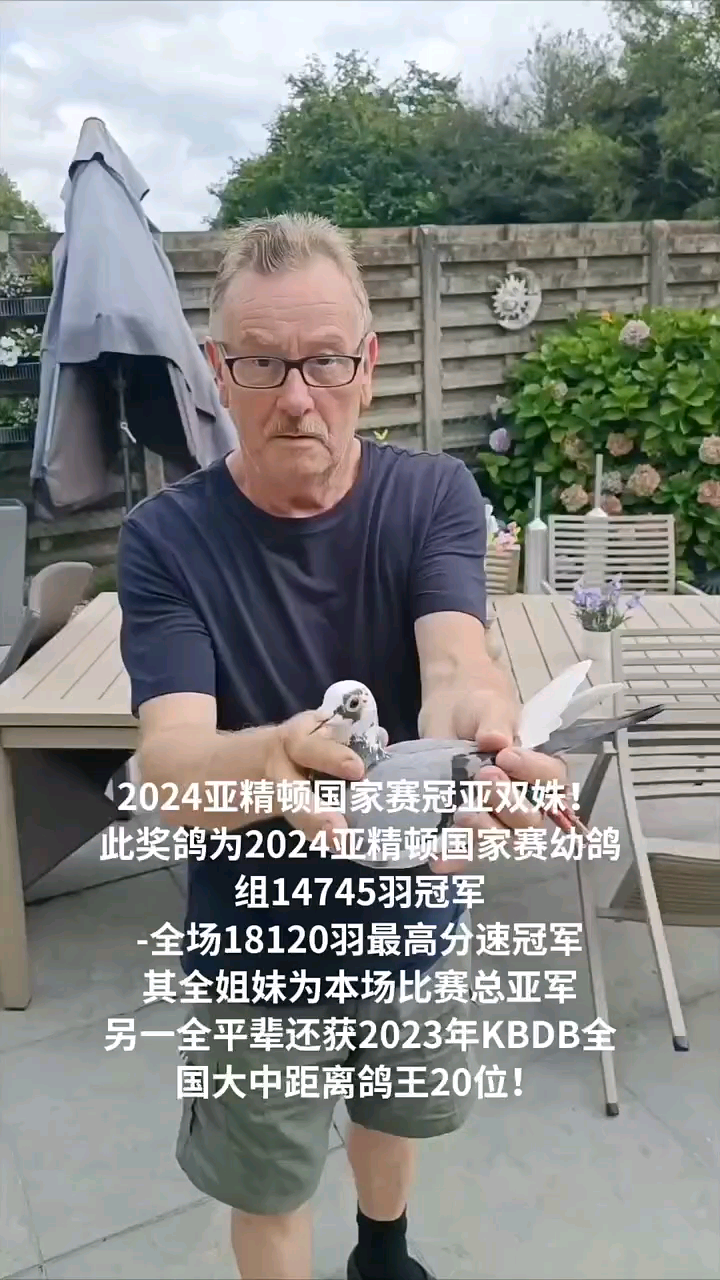连载(一)
妻子在撞墙,用她的背部,背的上中下部、左右肩胛和左右侧背。人肉与墙体制造出钝钝的撞击声。她的表情庄重沉着,眼睛偶尔瞟一下定时器。二十分钟,一个被严格设置的时间长度。
穆先生把电视设置成静音,耐心地翻频道:电视导购饶舌的喜感,谈话节目的敷衍掌声,折子戏扭着走形的身段重温陈年旧梦……可以说毫无意义。
意义。穆先生把这个词埋在肚子里,怕说出来给人笑话了。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他被这个不实用的词给控制了,他怏怏不乐。也可能,跟人生所处的阶段有关:他的社会属性,固定了。所谓的前程,不用抬眼皮都能看到结尾:安全抵达退休;而家庭生活,从这个秋季起,也变得极其单薄:儿子到外地上大学了,随即成了他太平洋卡的附卡,其存在形式就是对账单上每月新增的几排数字。
很多人把这段时光唤作“第二春”,可这实际上是多么草木萧瑟、万物沉沦的春。
穆先生不喜欢上班了。他不愿意看到那些新晋者或即将新晋者的面孔,轻浮得富有生机,握着早饭在电梯里嘎嘎笑、谈论昨夜的加班,脸上的疲惫如新款镜架般闪光。这刺痛他的眼。还有他们的早饭:街头的、仓促的、却带着油炸葱花的快活劲儿,在狭小的电梯间里粗陋地钻入鼻孔。这使他加倍地感到被冒犯,同时又莫名其妙蔑视起他自己的胃,那里早已装着四平八稳的早餐:新磨的豆浆,一只无公害农家草鸡蛋,黑米稀饭,另加一勺妻子自制的“固元膏”(据说此膏强健之效非凡,男女老少皆宜,全国大流行)。
没有办法,他醒得太早了,寂静得近乎空洞的家里,他醒来。脆弱而空虚,好像从未睡好,但也无需再睡。只有起来,只有跟妻子一块儿准备早餐,然后坐到餐桌边,把那该死的营养均衡的早饭给吃了。
多少次,他推开碗,赌气说他要到外面买一个薄脆的煎大饼或油炸糍粑,“管他妈的胆固醇与地沟油!”语气暴戾,好像这是了不起的反抗。妻子站在阳台上,一边梳头,一边咧了一下嘴,只当他在讲笑话。每天早上,妻子要用牛角梳梳头两百下,她也诚恳地动员穆先生梳,此类的动员还包括:背部撞墙(方法如本文开头所示,可通全身经络)、叩牙三百次(宜取仰卧体位,至口中生津,可固肾补肾)、饭后快走四十分钟(微喘、微汗,可消积化食)、热水泡脚(水深近膝、保持高温,可驱寒去火)、腹部揉摩(睡前与晨起,顺时针一百下,逆时针一百下,可调血健胃)……穆先生记不全了,当真-一一实施,他只怕自己会疯。但妻子说时,他能做到认真倾听,妻子的遣词完全是保健书上的说教套路,又带着江湖医生般的神神叨叨,听上去陌生而荒诞,真有些不敢相认。
--最近几年,妻子与“养生”有了瓜葛,其纵情的狂热十分惊人:任一张小报上看到合适的内容,剪下;每日上网浏览各种健康小窍门(这是她对网络的最大利用),并选其精华打印;隔一阵到书店带回几本畅销健康书,特别认真地读,像学生那样,画红线,加着重号……她开明地接纳各方面的学说,并且时常刷新,以新的理论覆盖旧的,更以亲身实践去考证或推翻。比如最近,她迷上的是“温度”学说,根据二十四节气变化、根据食苔之色(红、偏白、偏紫、厚腻、发黑)、根据手指甲(有无半月形、半月形大小、五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根据手掌上的青筋(有无、所出现的位置及其深浅)等一整套的标准,她让他狗一样伸出舌头,又算命先生般拉着他的手,细细研究,然后确定需要疏肝或是理气、除湿或是清热。那么,什么样的食物才一一对应呢?她另有一张大表,对每一种入口的东西,哪怕是酱油与茶,都精确地分成平、微温、温、热、凉、寒、大寒……整个体系极其庞杂而细微。
穆先生一度以为她是迷了心窍、要像范进那样给扇上一巴掌才好,如此地把肉身供奉着、伺弄着,不正常啊!整个人生岂不是本末倒置?可是很快,他惊讶地发现,妻子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群人,她是整个城市,她是举国上下,她是全球浪潮。晚上,穆先生被她拖着在小区“快走”,只见三五成群迎面而来的,莫不面色严峻大步流星;超市里,农场直销、有机食品与粗食摊子前,无数双手像溺水者那样地伸去;熟人席上相见,殷切地口耳相传:祛除百病的倒走运动、冷僻但神奇的牛蒡菜、全能西红柿、万恶之源的反式脂肪、维根素食主义……
显然,妻子是正确的、进步的、符合时代的。可问题是,这就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与全部过程?有谁注意精神那一方面的事情吗?是否贫血、缺钙、老化、脂肪堆积、病变生癌……穆先生不敢问,怕看到妻子惊讶到像是同情的目光。可他知道,内心深处,他与妻子不在一块儿,甚至,她让他对肉身产生了逆反性的憎恨,绵软但坚决的恨。
憎恨的外在表现就是反胃:工作、同事、家,妻子、儿子、吃饭、睡眠、运动,电视、报纸--真像最糟糕的自助餐啊,盘千里全有,可他索然无味,什么也不想碰。
从阳台上往外看时,他注意到那群鸽子。唉,鸽子,只有像他这样把目光投向虚空的人,才会注意到吧。
阳台外的虚空,呈现为使人疯癫的复制--小区里,一排排相邻着的灰色屋顶下,那紧闭的门窗里,全是一模一样的户型,洗碗池的下水道、电视与沙发的距离、床的朝向、马桶的坑距……他相信,敲开任何一家的门,打开冰箱,都可以取出同样一瓶开了口的“四季宝”花生酱;拉开衣柜,会在同一个位置找到“AB”内衣;而次卧的书桌上,被翻烂的课本内页夹着同样一份奥数课时表……这是样板化与标准化的要素,被切割被压榨下的生活,人人面目含糊!也许,他、妻子,以及儿子,可以任意进入某间房子,与里面的主人互为置换,错不了的,太阳照常升起,甜蜜照常流淌--这想法令他感到一阵惊惧,他怀疑自己的整个大半生,所过的都是公共的、他人的、典型化的物质生活,他从来就没有过真正自由的意志……
可是,鸽子!看哪。
正是黄昏时分,暮色灿烂而消极,那群鸽子就在对面的屋顶上。玲珑的身姿,纤巧的不停转动着的脑袋,饱满弧线的腹部,何其优雅而异样的美!它们起飞,它们落下,它们梳理羽毛,它们斜着身子在空中交错,它们突然从视线中飞走。
这骄傲而不规则的飞翔、失控般的消失--他妒忌!
站在密封阳台里,像关在动物园里的某种灵长类,四十七岁的穆先生偏着头痴望着--不禁想念起一个人,想得心中绞痛:那是从前的自己,很年轻的时候。那个他,有趣也有点神经质!那时的他过得狂放动荡、充满尘土与暴雨,蔑视规矩与价值,在战栗中虚掷时光!他写过长达二百六十行但全无韵脚的诗,献给一只长满癞疮、瘦骨嶙峋的野狗;他半夜里出发,沿着南京长江大桥跑步,被值勤的士兵追上并严厉盘问,他匿名给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同事写情书,真挚热烈,然后满意地看到她改变了十多年的旧发型;他心血来潮把自己弄成乡下穷光蛋的模样,在寒冷的晚上挨个儿搅和沿街的店铺,并像《百万英镑》里那样,在对方施以不屑时猛地掏出一大叠新票子。
那个自己,什么时候死的?一下子死的还是慢慢死的?竟都记不清了,也不重要了,总之,被另一个驯化的家伙取而代之了,迅速而彻底进入了一个绿色通道,通往稳妥的工作、讲究卫生的妻子、好地段的房、有出息的儿子、洗得干净的车,然后,到了现在,以及……将至的终点。
呸,真不愿承认这样的自己!恨不得断绝关系!一个人该怎么与自己断绝关系?直接掐死吗?这想法有点阴冷,但也很亲切--他重新往鸽子们看去,那里已经空了,夜幕垂挂,它们归巢了。眼前的屋顶重新变得平庸、荒凉。像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角落一样,不值得用眼光去停留。
就在转身的一刻,穆先生却忽地看见了最后一只鸽子,正滑翔着飞过,灰色,尾部一圈黑色的“叉”形花纹,像在宣布:错!错!错!穆先生身子不动,只用余光追随,随即,他吃惊地发现,那鸽子所回归的巢,离他很近--就在隔壁单元的顶楼,怎么以前从未留意到?
穆先生仰头看,那家顶楼的露台挺大,紧凑地堆放着若干排铁灰色的鸽子笼。鸽子们正停在笼子顶部或边缘,发出温柔的令人心痒的咕咕声,细脖子上一圈异色的羽毛在即将消逝的光线中流溢出令人惊讶的光泽。
穆先生忽觉嗓眼里不适,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也咽下某种愉悦的期待:此一瞬间,突然像是有一些意义了。
晚餐是蒸山芋和脱脂酸奶,餐桌上十分清贫。饭食现在经常如此,古怪但无法责难的搭配:五种豆子加三种杂粮熬成的粥;嫩玉米清汤;豆渣燕麦团子;加了蒜泥的土豆泥;水煮各种蔬菜。糙米饭。妻子的理论是: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总比生病了吃药强。
“每顿五百克山芋加二百五十毫升酸奶,这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排毒餐,连吃两个晚上,次日就可以清除出一公斤的宿便。”妻子满脸确凿。
“重量怎么把握的呢?”穆先生尽量提起精神,表现出天真的兴趣。
“超市标签上都打重量的呀,算一算也就出来了。不过,我还真想买个家用小磅秤,那样更方便。快吃吧,山芋要连皮吃!”
“我是问排出的宿便,那个一公斤怎么……”
“别闹了,这在吃饭呢。”妻子拿起她的“饭”,黄灿灿的山芋。
实际上,穆先生想问妻子另一个问题,想问很久了:“嗳,我说,你真觉得,这样围绕着身体忙乎……是件头等重要的事?”
“想什么呢……还用说嘛!我们这岁数……”妻子缓慢地细嚼慢咽,每一口嚼二十下,当然她并不真的数,但保持那种计数般的节奏,看上去像是在嚼油渣、口香糖或是其他难以下咽的东西。
“你一点不觉得,这有点可笑?而且……越想越觉得这挺没劲的?挺……”穆先生说着,自己也停下了。他发现这是块抓不着的痒,他没法确定,在这具好吃好喝的肉皮囊之外,他到底想要什么?他所消沉与焦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很难跟妻子,或是跟任何一个人说!
毒子笑了:“所以说呢,你就是太有闲劲儿了!待会儿跟我做拍肩操吧,散出汗来。身体多动动,脑子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谈话像进入了十字路口,他眼巴巴地站在西边,妻子却满面笑容地往东拐。这不是第一次了,这还将有很多次。穆先生改变话题:“对了,看到一群鸽子,就在我们……”
“哦,那个!怎么才看到?就是旁边那个单元,六楼那家!我知道有不少人到物业投诉!也有找我反映的,鸽子也会传染病毒你知道吗?它们的粪便、羽毛,还到处飞、到处啄,比鸡可危险多了!一有什么疫情,可就倒霉了!偏偏还在我们家楼上!”妻子是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她有些忧心。
“但……它们,很美。”穆先生小心地遣词。实际上,他想他不该跟妻子谈起它们。新话题是还是一个十字路口。
“……不过,鸽子肉可是好东西!性平、温补,‘一鸽胜九鸡',不得了的好啊!鸽子蛋更好,外面一个鸽子蛋的价格可以买一斤半鸡蛋!”妻子又带着冲往下一个十字路口。“你说,我们能跟他直接买吗?鸽子最好,鸽子蛋也行!那可是一顶一的新鲜!外面许多鸽子蛋都是人工的,多可怕。”
“我们……不认识。”穆先生终于吃完了他的五百克连皮山芋。
“那就搭搭话好了,你不正好无聊得很嘛。你就跟他说,我可从来没有把投诉转给物业。”妻子找到了友好睦邻的突破口,笑嘻嘻的。她正在喝一勺果醋,据说这最利于平坦腹部。
作家鲁敏:
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现居南京,业余写作。
1991年起开始散文创作,以书评、随笔、美论为主,作品散见《美文》、《散文百家》、《书与人》、《艺术世界》等报刊杂志,此间八年,作品发表量15万字左右。1999年,偶起小说写作之念,迄今共创作小说80万字,代表作有《白围脖》、《轻佻的祷词》、《镜中姐妹》、《笑贫记》、《白天不懂夜的黑》、《方向盘》等,主要刊发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花城》、《山花》等杂志,并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中华文学选刊》等出版物选用或连载。中篇小说《白围脖》曾获第五届南京市政府艺术奖金奖、第五届金陵文学奖荣誉奖,中篇小说《男人是水、女人是油》获第11届百花奖入围奖。
2004年底,长篇小说《戒指》在《十月》长篇增刊发表,次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长篇小说《爱战无赢》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增刊发表,同年5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鲁敏小说以中国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世象百态为描摹蓝本,笔墨触及城市贫民、伪中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市场商贾等各个阶层,着重透视物质生活中个体心灵史的妥协与飘零。
主要作品目录:
短篇:
《转瞬即逝》《雨花》(2000/12)
《寻找李麦》《小说家》(2001/2)
《宽恕》《十月》(2001/6)
《紊乱》《北京文学》(2002/2)
《冷风拂面》《十月》(2001/6)
《我是飞鸟我是箭》《小说界》(2002/5)
《虚线》《山花》(2002/5)
《左手》《青年文学》(2002/7)
《把爱情泡茶喝了吧》《小说家》(2002/4)(原名《将饮茶》)
《头发长了》《长城》(2003/1)
《四重奏》《人民文学》(2003/6)
《李麦归来》《青年文学》(2004/6)
《摇篮里的谎言》《小说界》(2004/2)
《白天不懂夜的黑》《芙蓉》(2003/3)
《天衣有缝》《钟山》(2003/2)
《心花怒放》《长江文艺》(2005/7)
《杜马情史》《青年文学》(2003/8)
《未卜》《山花》(2004/2)
《灰娘娘》《江南》(2004/5)
《小径分叉的死亡》《人民文学》(2005/4)
《方向盘》《人民文学》(2005/8)(原名《没有方向的盘》)
中篇:
《亲吻整个世界》《山西文学》(2001/2)
《白围脖》《人民文学》(2002/3)(原名《悼词》)
《青丝》《花城》(2003/5)(原名《青丝白发》)
《镜中姐妹》《十月》(2003/4)(原名《爱与哀愁》)
《温情的咒语》《小说月报?原创版》(2003/6)
《轻佻的祷词》《小说月报?原创版》(2004/4)
《男人是水,女人是油》《人民文学》(2004/8)(原名《向中产阶级致敬》)
《笑贫记》《十月》中篇增刊
长篇:
《戒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爱战无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