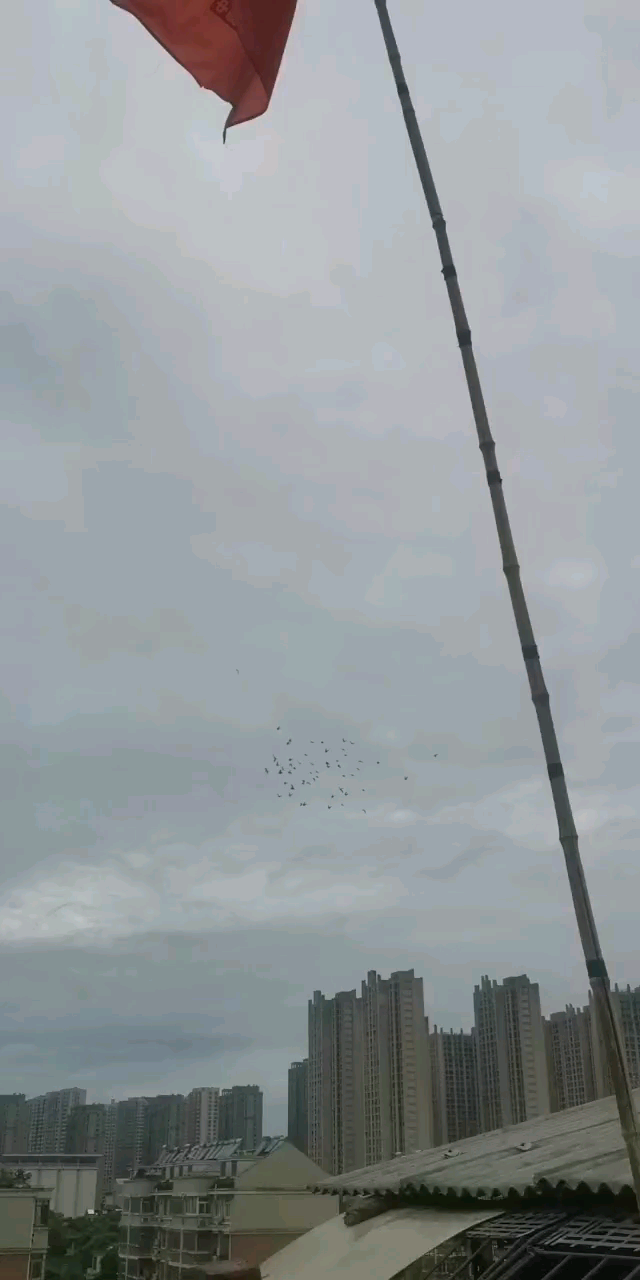那天我是坐夜车离开北京的。
上午,我下了火车直接去省体育局信鸽协会,我要见欧阳秘书长,我要把情况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我很想见他,因为我想此时他也一定需要我。可是,我敲响了半天欧阳秘书长紧闭的办公室的房门,办公室内却没有回应,显然,欧阳秘书长不在。
欧阳秘书长办公室隔壁房间的房门开了,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看了看我,然后自言自语道:“怪了,今天找欧阳的人能有一个排了。”
我忙问:“欧阳秘书长他没来上班?”
年轻人又上下打量我一番,摇了摇头说:“我没看见他来,刚才不少人都找他,现在大门口台阶上坐着的那个老头也是找欧阳的。”
我顺着年轻人手指的方向向大门口年看去,见台阶上果然坐着一个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式军用大衣的老者。坐在那里的老者像一尊雕像。
年轻人接着说:“这老头真犟,大清早,还没到上班时间,他就一脸的怒气来了,敲了半天欧阳办公室的门没敲开,转身又去敲咱局长的办公室门,局长也不在,他怒了,他说他一定要等局长回来。这不,在那坐半天了。”
听了年轻人的话,我想了想,然后走到了老者身边,并挨着老者坐在了台阶上。
老者翻眼看了看我,然后又紧了紧身上有些破旧的老式军用大衣,便转过身去。
东北的春天,乍暧还寒,显然老者坐的时间久了,感觉有些冷了。
我掏出了香烟,一边递给老者,一边问:“爷们儿,是来找欧阳的吧?”
老者瞅了瞅我递上的香烟,不动声色,然后掏出了一个旱烟口袋,瞬间就拧成了一只很规范旱烟,点燃后大口地抽了起来。
“给我也拧一袋吧?”我跟老者套近乎。
老者头也没抬地给我拧了一袋旱烟,递给我后,语调低沉地问我:“你也是来找欧阳秘书长的?”
我点了点头:“是,我是刚从北京回来,下了火车就直接来了,我想问个明白,这么好的一个秘书长为什么说撤就给撤了,为什么……”
“就是!”我的话把老者激怒了,他打断了我的话,“娘的,刚刚看到点希望,就他娘的完蛋了,还他娘的有没有王法!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去找欧阳秘书长,欧阳秘书长不在,我去找局长,局长也不在,今天我就是死也要把局长等回来,一定要问个明白。”
老者一脸的怒气。
我仔细地打量起老者,面前的老者一张布满沧桑的脸上爬满了皱纹,一双充满愤怒的眼里闪着疑惑。我估计老者有80多岁了。
我问:“爷们儿,您认识欧阳秘书长?”
老者摇了摇头:“没见过,但鸽友谁不知道他,是条不可多得的汉子,是个替咱鸽友想事做事的好人,他上任没几天就做了那么多有利咱鸽友的好事,处处替咱们鸽友着想,比如推广奖金赛,多好的想法,看那些黑心老板还怎么作弊,娘的,我琢磨就是因为他的举动断了那些黑心公棚老板的财路,所以,他们走通局长,局长真他娘的不问青红皂白,真就把欧阳秘书长撤掉了,还他娘的有道理讲吗!肯定是局长和公棚老板有猫腻!”
老者的旱烟真冲,抽了两口就呛得我一阵咳嗽,好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问老者:“爷们儿,您也一定养鸽子吧?”
听了我的话,老者一脸的无奈:“养,养了一辈子,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就养,你算算是不是一辈子了?到头来养得伤透了心。好容易盼来了个替咱鸽友说话欧阳秘书长,有机会参加一次公正、透明的比赛,不管输赢,咱心里服气,我就是死了心里也净了,可是……”
老者说着有些伤感地叹了口了气,然后有些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发现老者动了真感情,因为老者的眼窝明地湿润了。
此时,我的心也如同刀绞一样的疼,我不想安慰面前的老者,因为此时我的感受和老者一样。我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者为我拧的旱烟,心中在默默地流泪。
老者按灭了手中的烟屁股,仍然是一脸的怒气,他的语调很低沉,看得出他的内心很难过:“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看到今天这些奇怪的现象,心里犯堵呀!那个年头我们面对死亡,没有谁怕过,脑子里只有一根式筋,拼着命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江山属于咱老百姓的了,可是,你看看那些做官的,泡着茶,抽着烟,聊着天,我们枪林弹雨把江山打下来了,倒让这帮混蛋享清福,他们哪有几个干正事的,更可恨的是不但他们自己不干正事,还他娘的不让想干正事的人干正事。就说欧阳秘书长吧,真正想为咱鸽友办点正事,可是,当官的不让呀!这不,说撤就给撤了。你说他娘的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细细品味着老者的话,心里仍然在不住流泪,不,是在流血。
老者又拧了一袋旱烟,大口地吸着,接着说:“今天我就是死在这里也要把局长等回来,我要他给我个说法!”
老者的话说得十分坚定。
我抬起头,认真地看着老者,然后一字一板地说:“我跟你一起等!”
……
后记
小说写这里应该算写完了,可是,我的几个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看了后几乎是异口同声,说这是一部没有结尾的小说。无奈,只有又补充了这么个后记。
那天,我和老者没能等来局长,天大黑了,体育局的大楼内早就人走楼空了,可是,老者说死不走,他说,今天等不来还有明天,明天等不来还有后天,总之,他一定要在这儿等下去。我劝老者今天就不要再等下去,明天再说吧,咱总不能在这里毫无代价地坐一宿吧。在我的一再说服之下,老者才忿忿地离开,临走时还一再说,明天一大早他就来,他就不相信他等不来局长。至于以后老者见没见到局长,见到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不清楚了,因为后来我再也没去过体育局,也没见到过那个固执而又倔强的老者。
我把拯救中国鸽界的希望再次地寄托在了铁姐身上,那天,我再次去北京,去找铁姐。闲暇之时,我去了中国最著名的一家大公棚,因为那天那里正在进行令人关注的500公里决赛。关于这家公棚,称得上是咱们国家起步最早、最具影响力、奖金总额最高的公棚,在这家公棚里也传出过不少作弊丑闻,而且传得有根有梢,可是,最终却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以不了了之而收场。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家公棚的饲养员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欧阳铁权,我惊呆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