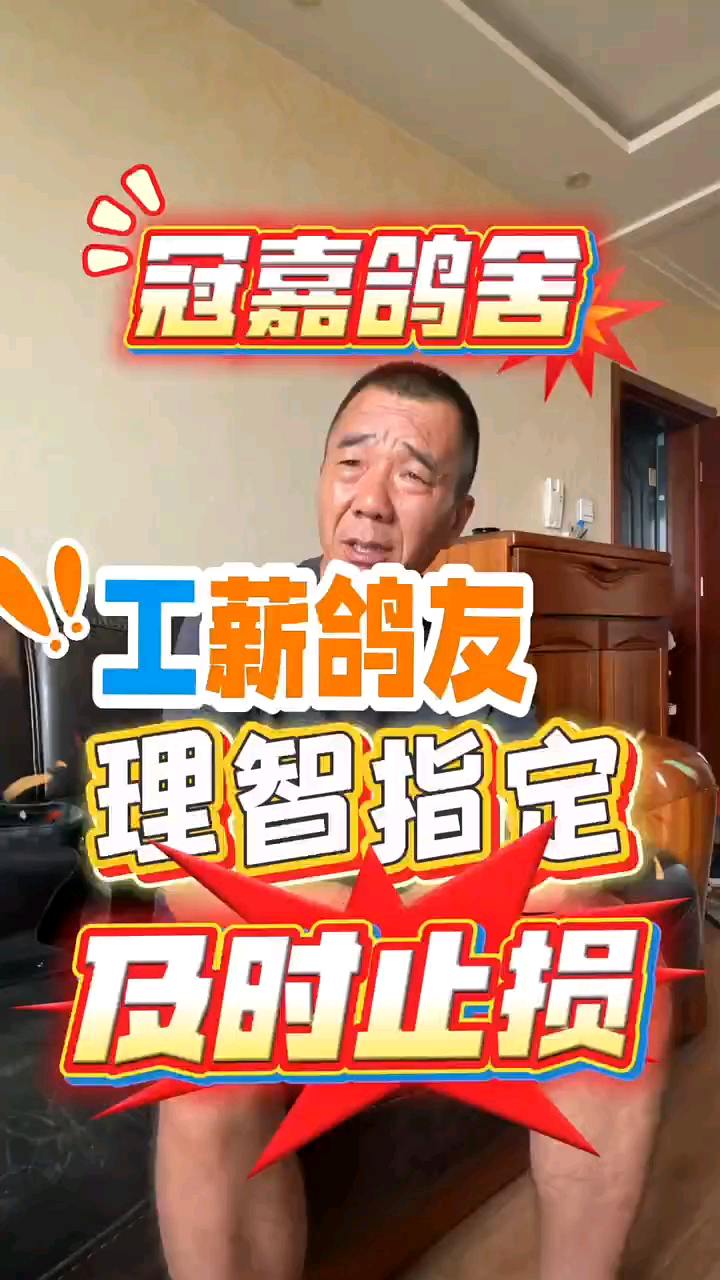小传:王世襄,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1914年出生于京城官宦世家,燕京大学文学硕士。1945年担任追回战时损失文物工作。之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等。王世襄兴趣爱好广泛,精通漆器、竹刻、明式家具、传统工艺等诸多领域,编写有四十多本著作。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研究,他曾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及“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奖”。
抢救鸽子
王世襄老人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无论是家具、漆器、竹刻,还是蟋蟀、鸽子、老鹰,在他的笔下,全都成了一门门精深的学问。采访老爷子可不容易,好不容易约定了时间,听说他又把腰给扭伤了。这腰怎么扭的呢?据他家人说,在奥运期间,家里人不愿让他熬夜,但是他半夜三点钟又悄悄地爬起来看女子网球的决赛,结果不小心把腰给扭了。
杨澜(以下简称“杨”):您提议在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放中国的观赏鸽是吧
王世襄(以下尊称“王老”):对对,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有观赏鸽,就知道有信鸽,有和平鸽,其实那就是吃货。那些唱歌的小孩拿鸽子也不会拿,鸽子就瞎挣,唱完了一放……电视上也是。我都跟方宏进提过意见,我说原来你们《东方时空》演升旗,多庄严,一会壮丽山河,一会长城,老远飞过来一个鸽子,等飞过来一看:吃货!我说中国有那么多好鸽子你不在镜头上放,你弄个吃货在这儿,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侮辱,我接受不了。
杨:观赏鸽,这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也不明白,这跟和平鸽和信鸽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就有文化意义?
王老: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多少代传下来的。五代那个黄筌,他几个儿子都是名画家,他画了很多画,画的什么呢?《金盆鹁鸽图》,一个金盆,鸽子在里头洗澡,上面配着花,旁边有竹子,有石头,很美。那鸽子绝对不是普通的鸽子。
杨:绝对都是名种培育出来的。
王老:而且这个种类,也有灭绝了的,也有新种出来的,很有讲究,嘴要什么样,眼睛要什么样,眼珠要什么样,头型要什么样,花的颜色部位也都有一定讲究,连脚趾甲什么样都有要求,这完完全全是中国的鸽子文化。那么将来2008年,作为国家主办的奥运会,你当然应该宣传本国文化,是不是?张艺谋要是管这事,他也得从这儿着想。
杨:那您为什么觉得鸽子在开幕式上就一定很重要呢?
王老:因为这鸽子是传统鸽子,跟外国鸽子不一样,花色不一样,养好了,可以一盘白的,一盘灰的,一盘紫的。而且它不像信鸽一样,信鸽一放,都跑了,都走了,它可以围那儿转,它带着鸽哨,鸽哨还特好听。鸽哨是和平的音。而且这个鸽哨外国没有,只有中国兴这个。
杨:那其他的鸽子就不会绕着转?
王老:不会,其他的鸽子在你家里头可以绕着转,它围着你家转,可是要是别处养的鸽子,一放它就飞走了。所以在这个奥运村附近,应该有几个地方有计划地养不同颜色的鸽子,完了,一盘飞起来,一盘飞起来,再合在一块儿。
杨:那这花费很贵吗?
王老:这花费比起足球队那是九牛一毛了。
杨:您知道足球队贵啊?
王老:不用说足球队了,它比任何一个项目都便宜。你现在弄这个大跑车,花多少钱啦?那玩意儿真玄,说撞死就撞死。
杨:那要的是另一种刺激。
王老:其实我出这主意还不是为奥运会,我想借这个题目,保存观赏鸽。假如听我的,那养了不就变相把这个传统保护下来了?你别等它绝了种,再去找,那时候没有了。
杨: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鸽子的不解之缘呢
王老:从小我就上房轰鸽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好容易买了一对鸽子,结果膀子没捆好,一下都飞了,我还大哭了一场。少年玩家
王世襄的父亲是外交使节,母亲是画坛才女,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和西式教育的双重熏陶,但天性活泼的王世襄却一心只问窗外事———“斗蟋蟀、养獾狗、学摔跤、放大鹰”。他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玩家。
杨:我看您大学那张照片,手上就架了一个鹰,那感觉挺像八旗子弟的。
王老:我从小学一直玩到大学毕业。1934年到1938年我念大学,中间还念了两年预科,让燕京大学预科把我刷出来了。燕京有这么一个规矩,说你要是两门不及格,就要开除。可是这之前还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别的科分数比较好,如果有,就问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愿意转,再让你转过去试试。这样我就转到国文科念语文了。到了念语文的时候,我虽然是贪玩,但诗词歌赋我全会,我就成尖子了,更不好好学了,而且整班的学生诗词都是我代笔。女生的诗词,我还给她每人一个格调,按她的格调给她,让老师发觉不了。
杨:那您在全班女生中非常受欢迎了?
王老:受欢迎是受欢迎,不过男生女生我都是整个包了的,所以顾随先生就说,我教了这么些年,没教到一个班有这么好的。
杨:敢情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王老:这是说笑话了。
杨:母亲后来去世给您很大的打击?
王老:母亲去世那年,我考上研究院了。我母亲1939年去世,她去世后,我就觉得,她这么培养我、希望我,又这么放纵我,让我玩,我要再这么下去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师,所以我幡然改悔,狗成了看家狗,鹰也不养了,鸽子也送人了,我是整个一个大转变,什么都不玩了,专心写论文。
李庄被拒
当时的北平,已经身处沦陷区,王世襄却一心沉醉在中国古代绘画的意境之中。1943年,带着花费5年心血写成的论文手稿,他穿越日军封锁线,来到了西南大后方,寻找自己的文化理想。
王老:我到了四川李庄,那是一个后方的学术中心,当时最高学府一些最有学问的人都聚集在李庄,包括傅斯年这些人,也都在李庄。
杨:傅斯年先生曾经也断然不要您,是吧。(王老:对对。)您好像也被这些大学问家拒之于门外,这对您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老:他就问我一句话:“你哪儿毕业的?”我说燕京毕业的,他说燕京毕业的不配上我这儿来。
杨:他只要清华的,是吧?
王老:他要清华的,要北大的。
杨:那您那时候生气不生气?觉得窝囊不窝囊,委屈不委屈?
王老:那我就回头走呗,就别再说了,没的可说了。我跟梁思成先生说:干脆我就上你的营造学社吧?他就把我留下了。后来日本一投降,他们就派我接收文物,三个点,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那两个点都没成绩。我拿回几千件国宝来,有杨宁史的铜器,有溥仪存在天津张园家的东西,还有朱桂老(朱启钤)的缂丝。东西在长春,那儿已经被包围了,朱桂老怕炸弹一来,他的东西都毁了,忽然有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来,说宋美龄要过来了,你赶紧来,写个情况,请她赶紧把东西给运出去。我说我上哪儿找宋美龄去?他说你甭管了,你写完了送给我,我有法儿交。所以我就写了,没两天就有专机把东西送到故宫了。
“三反”恶梦
1946年,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父辈的文物渊源、追寻国宝的辉煌经历以及文化人的追求,使他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不惜从登记卡片、分类、造册、清理院子做起。不过,美丽的故宫之梦,却很快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
杨:您当时没有想到,后来就是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
王老:你有理说不清。那时候阶级斗争讲成分,我又是在美国学校上学,又是官宦出身,期间又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去参观博物馆一年,父亲又是外交官……他们跟我说:国民党没有不贪污的,而你是接收大员———其实我是一个助理代表,是一个小蹦豆子,我也不是国民党员。
杨:您那个时候解释不清这些事吗?
王老:你解释他不听你的呀,“打老虎”,就不讲理。
杨:“三反”的时候,您才40多岁吧?
王老:40刚出头。
杨: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壮年的时候,让您打道回府,回家了,有十年的时间跟文物没关系。
王老:而且手铐脚镣10个月,在(狱)里头得了肺病。
杨:您那时候有没有想不开的时候,想到过死吗?
王老:没有。受这种莫名其妙、极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有的人是自寻短见,老舍、陈梦家都自杀了;有的人是铤而走险,就是说:我跟你拼了。我觉得这两样都不能。你要自杀了,你不是等于自绝于人民?你要是铤而走险就更不行了。
杨:我估计您也没工具。
王:那倒不是,我想好了,我说我要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仅这样还不行,你无补于事呀,你不是白活一辈子?我就想,我在哪方面可以做点事?我想我对国家还是有益的。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写书。可是你这么做还得受好多好多的责难,弄不好就开斗争会。比方说我那书人家不能给出版,我就到刻蜡版的誊印社去自己刻,但当时我不知道有规矩,凡是单位的人拿了东西到那儿刻,他们要送到你单位的党委让党委审查,看你有没有反动思想。后来我在单位碰见誊印社的人,我说你干吗来了?他说我照例行事啊,你在我们这儿刻蜡版,我们得上你们这儿汇报啊,得让你们党委看哪。我傻了眼了。
杨:在您最困难的这个时候,您老伴抱怨过吗?
王老:老伴不抱怨,我们都是逆来顺受。比方说那个时候我要写东西,电灯泡供应很紧张,要个电灯泡,合作社不卖,得上街道老太太那开个条。可是我们老伴画图画了一夜,灯泡的质量不好,没用几天就坏了。坏了就再买去,这老太太说:“怎么又坏了,不给了。”
杨:开条去,哈哈。
捡破烂
王世襄是乐观和坚强的。在逐渐走出蒙冤的阴影后,他的生活情趣也开始慢慢恢复,逛古董店,钻小摊市,不亦乐乎。
杨:您那时候生活很拮据,政治上也不得意,还要花些钱去做收藏,怎么弄啊?虽然说那时候不像现在要价那么高,但也得花钱啊。
王老:我就捡破烂啊。我父亲也说了:你在我这儿白住、白吃,已经是占很大的便宜了,你要是再买玩意儿,我可管不了你。这他都说了话的,因为做这个没底,你今天买了,明天还买,所以我老伴也是新衣服都舍不得做,一切从俭。可是我买来的都是什么破桌子、烂板凳———我认识东西———我把它修理了。真的贵的、好的东西,我还是买不
起,不过我会成天骑着车满处跑,满处钻,别人看不到的,我能把它挖出来。
杨:有哪些地方是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王老:比方说上宝坻县。什么时候去呢?春节放假去,小店里住着,没火,炕上没枕头,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搁在炕沿上当枕头。那时候精力也充沛,很有意思,很好玩。
捐赠收藏
经过王世襄耐心细致的修整、考证、丈量、绘图,那些不起眼的“破烂”成了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也成了巧夺天工的家具圣经,在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文物界刮起了一股反响巨大的明式家具热潮。可以说,明式家具是王世襄最引以为傲的文物研究成果,也是最凝聚他心血的收藏。然而,90年代初,他却把伴随自己半个世纪的79件家具全部割爱给了在香港的友人,运到了上海博物馆。
王老: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们有一个条件,你花钱可你不能留,你得全部给博物馆,这是我惟一的条件,你要同意,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就这么达成了协议,我所得的是国际行情的1/10。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留了呢?也有好些原因,我的房子都让房管局给挤走了,我这些家具堆在我的上房里头,上房后头有5家人的小厨房都贴在我的后墙上,离我的房檐不到1米,任何一家要着了火,我这房子就没了,那家具也就烧了,我这一辈子的心血也就没了。我向文物局汇报这事,局长也没办法。那我就得想法处理了,不处理很可能出问题呀。
杨:拉走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觉?
王老:那也无所谓,照我说呀,这个东西占有是次要的,主要是你通过它能得到研究,得到欣赏,我这个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相濡以沫
王世襄一生的爱好和追求曾被妻子袁荃猷用纸刻作品传神地表现出来,挂在大树上的果实中。不仅有家具、竹刻、漆器这样的大学问,也有鸽哨、葫芦、獾狗这些逐渐被人遗忘的民俗绝学。2003年秋天,这位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近60年的老伴,这位心有灵犀的知音,永远地离王世襄而去了。
杨:您当初在大学校园里追求她的时候,还是以玩儿著称的吧?
王老:她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不玩了。她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她要编一个小学绘画的教材,燕京没有搞美术的,她那个系主任就说:让王世襄当你的导师得了。
杨:所以您就公私兼顾了?
王老: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有别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上南方了,后来又有了一个,也没成。
杨:我知道您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葫芦,给她装了一葫芦红豆,还挺浪漫的。
王老:我做了一对盒子,是拿那葫芦片拉下来拼的,我拿红木旋了以后镶在那儿了,烫上花——烫花是专门的一种火绘,北京只有三人会火绘,我是其中之一。后来我父亲生日,我把这对盒送他了。等她一回来,我就跟父亲又要回来了。
杨:送女朋友。
王老:父亲也赞成,也没为这个生气,这也是一个笑话。
杨:您的夫人做了什么特别让您感动的事?
王老:那感动的事太多了。最近我写了一个组诗,她那首诗是其中之一,我可以背给你听听。我说:
君曾一再言,
平生有二好。
访古摹饰纹,
游山写石貌。
一自助著书,
制图兼编校。(她死前去医院那天,还带
着病校完了一本书,)
伏案年复年,
勤劳致衰耗。
二好愿未酬,(她为了编我的书,不能去逛博物馆,不能去看山,也不能去旅游,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她。)
我痛难偿报。(我自己恨我现在没法补偿她呀。)
这是我给她写的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