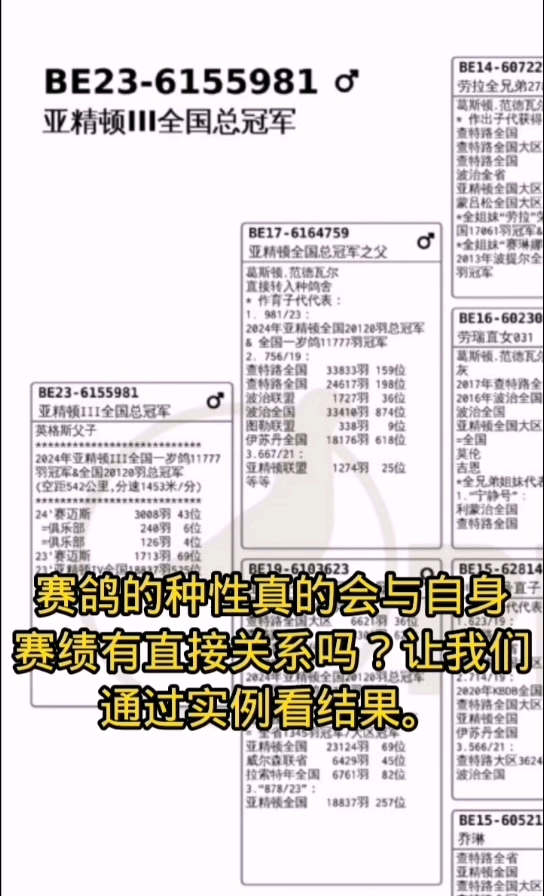20东方赛鸽公棚
1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晚,晚来的秋天让荣城更像一个迟暮的美人。每到秋日的黄昏,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不经意间盈满丁胜男的心尖。天依旧热着,可一早一晚就凉了许多。在这个秋日的黄昏,丁胜男出神地望着田野尽头渐渐沉下去的夕阳,脑海中几乎是空白一片,她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分不清日出和日落,总觉得日出日落没有多大的区别。
荣思浓、何晓亮、林云天、孙巧云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丁胜男懒得听他们说什么,她知道他们在筹划一个什么公棚,也弄明白了他们那个所谓的公棚不过是把别人的幼鸽集中到一个地方来饲养,当然,每交来一个鸽子要收取一定的参赛费。到了鸽子能比赛的鸽龄,由这个公棚统一训放,然后再比赛。比赛结束后,所有获奖的鸽子进行拍卖,拍卖所得款项百分之七十归交鸽子的鸽友,百分之三十归所谓的公棚。与家里养鸽子最大的区别是,所有的鸽子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饲养、同样的比赛距离比赛。用他们的话说,这样的比赛非常公道。
丁胜男知道这个主意准是那个台湾人林云天出的,而投资方一定是她的母亲荣思浓。那边的声音大了,他们似乎是在为奖金的设置争论。林云天软软的声音传过来:“奖金必须要设得高一些,这样才会有冲击力,才会抓住鸽友的眼球。”荣思浓说:“奖金设得高,那参赛费又要收多少呢?收得高了,没人来参加比赛,收得低了,就要赔钱。再者,我们的监管单位省体委早就说过,比赛的规程出来后,必须把奖金打到他们的帐户上,由他们监管,比赛的裁判也是由他们委派。这样的话,如果奖金设得高了,只有硬着头皮赔钱了。”
林云天说:“不论做任何生意都是有风险的,只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行了。”荣思浓说:“怎么把风险降到最低呢?”林云天说:“如果奖金设出六十万,每羽鸽子按三百六十块钱收费,只要能够收到两千羽鸽子就能持平。你算一算,一羽鸽子三百六,两千羽鸽子就是七十二万,去掉奖金后,还能剩下十二万,饲养管理这些鸽子有六万块钱就够了,是不是还有六万块钱的利润?而另一部分的利润就是获奖鸽拍卖,以及迟归鸽的领取,若拍卖底价是三百块,获奖名额设到一百五十个,那你又有多少利润呢?迟归鸽每羽三十块钱让参赛者自己领回去,又有多少利润呢?”
荣思浓说:“那获奖鸽若拍卖不了怎么办?”
林云天笑着说:“那有什么难的,让参赛者掏一百块领回去。”
荣思浓说:“说到现在,你还是没有讲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
林云天说:“我可以帮你从台湾、欧洲、美国等地联络一批鸽子。”
荣思浓早就觉察到做公棚准会有商机,她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抻一抻林云天,想知道他这几年来如此热心地关注甚至赞助荣城鸽会比赛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就是为打开大陆这块信鸽市场吗?以她的角度看,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这项工程过于宏伟了,他改变的可是大陆鸽友几十年的思维呀。另外,她还想利用林云天收一部分境外的鸽子。境外的鸽子越多,在荣城乃至全国造成的声势就会越大,声势越大,事情也就越好做了。那时,这些境外鸽子创造的价值早就不再是它本身那点参赛费了。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始终不大相信境外的鸽子在500公里的距程有压倒性的优势,她想亲眼看一看境外鸽子的表现。
林云天的心里早就盘算过,他这几年,连着在大陆砸进了将近三十万赞助鸽会比赛,可大陆的局面并没有打开,大陆的鸽友还是沉湎于超远程的比赛。在超远程比赛中,欧洲以及台湾的鸽子基本处于劣势。如果把公棚做起来,让巨额的奖金去刺激大陆的鸽友,让大陆的商人看到做公棚的利润,那样的话,用不了几年,大陆的公棚就会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于大江南北,大陆鸽友的思维也会很快转变,这叫顺势而为。到了那时,他的商机无限,这块蛋糕实在是太大了。
荣思浓并不是一个容易说服的人,最起码现在看是这样的。林云天又抛出一个诱人的条件,他说:“荣老板,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为了大陆的信鸽事业,我愿意出资三十万作为启动这家公棚的基金,你的公棚什么时候赢利了,什么时候再返还给我。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也可以算是我在这家的投资。”
荣思浓沉吟了片刻,笑着说:“林老板,你的心意我领了,在国内做公棚,我们是第一家,风险肯定小不了,哪能让你一个台胞承担这风险呢。我看这样吧,不论这公棚做得好与不好,我在三年之内返还您的三十万,另外还付给您利息。”
事情就这样彻底敲定下来。
早在几天前,荣思浓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她不可能,也没时间天天耗在这个公棚里,让谁管理这个公棚呢?人选其实早就有了,但她还有些吃不准。
一行人在聚得丰吃过饭,荣思浓对丁胜男说:“胜男,你陪妈妈走一走吧,让司机去送小何和林老板。”丁胜男点点头。从酒店里出来,外面早就是万家灯火了。
母女俩走了一段,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个路口,丁胜男忽然说:“妈,你觉得何晓亮这个人怎么样?”荣思浓瞧着远处悠悠道:“人倒是满不错,不过有点过于世故了,听说他还是个大学毕业生。”问过这话,丁胜男好长时间又没有说话。荣思浓侧过脸说:“胜男,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丁胜男扭捏道:“妈,你说什么呢?”荣思浓说:“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不论她自己说不说,她的脸上都清楚地写着呢,那个何晓亮跟你表过态吗?”丁胜男的脸腾地红了,她不知该怎么回答母亲这个问题,因为何晓亮确实没有对她表示过什么,但她又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向她表达着什么,有时不过是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有时只是轻轻地拉拉她的手。
荣思浓说:“胜男,妈有一个想法,想请何晓亮担任这个正在成立的公棚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丁胜男吃了一惊,她微微磕巴着说:“那,他、他愿意吗?”
荣思浓说:“我想他是会愿意的,一方面是你的缘故,另一方面,我也问过一些人,何晓亮虽说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可他所在的那个工厂的效益相当的不好,几乎只发放生活费,而他兼职的《南京赛鸽》杂志每月不过给他六百块钱,我还听说他的家境也不是很好。”
丁胜男诧异地瞧着母亲说:“妈,你怎知道的比我还多呢?”
荣思浓笑了,她的笑容中略带着几丝苦涩:“我这辈子亏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你父亲,我不愿意看到你将来离我那么远,更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的女儿一出嫁就过苦日子……”说到这里,她停顿了片刻说:“不说这些了,你今天晚上回家后,看看你爸爸对办公棚的看法,记着,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
丁胜男点了点头说:“妈,你真的和我爸爸再也走不到一起了?”
荣思浓幽幽道:“他是不会原谅我的,我对他的伤害太重了。”
2
何晓亮此次来荣城之前,与主编发生了一些摩擦。事情是这样的,主编听说他去荣城只是做一个采访稿,没有什么广告业务,有些心疼差旅费,就没有痛快地答应,用他的话说,不过是千把字的一个稿子,用得着跑一趟吗?
何晓亮费了半天的口舌,主编还是没有答应。他的话里话外还透漏出何晓亮去荣城别有用心。何晓亮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许多鸽友都喜欢给自己的爱鸽拍个照片,但他们又没有做广告的意图,他也就顺手牵羊地做着,额外挣点钱。主编对他的做法颇有微词,但一直没有挑明。刚才何晓亮的态度、口气稍嫌硬了些,主编也有点不高兴,话跟着就冒了出来。何晓亮不由得生了气,他说:“是的,我是在为杂志工作的同时也做了点自己的事,可你怎么不看看我给杂志创造出的价值又有多少呢?我既做记者,又做编辑,还兼着摄影,一个月才给六百块钱,是不是有点少呀?”主编看到何晓亮真的生气了,也有些后悔,他当然更清楚这份杂志现在是离不开这个有些讨厌的何晓亮。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既懂鸽子,又精通文字,还有一手拍摄鸽子的绝活。如果这小子一翻脸甩耙子不干了,那对杂志本身影响是相当的大。想到这一层,主编缓和了下口气说:“你要是非要去,那就去吧。”
何晓亮真正想去荣城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丁胜男。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他忽然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那个姑娘,想到爱,他又觉得自己很虚伪,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这个“爱”字或多或少还搀杂着一些其他的成分。也许他割舍不下的不仅仅是那姑娘。
此时的何晓亮正在丁家的客厅里与丁昊翔谈论着荣思浓的公棚。何晓亮说:“丁伯伯,假如公棚真的成立了,您觉得我们国内的鸽子能否战胜那些境外的鸽子?”丁昊翔凝视着墙上那副巨大的鸽子画像沉吟了很久才说:“怎么才能算是战胜?”何晓亮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如果把战胜定义为是谁得了冠军呢?”丁昊翔说:“一个冠军不代表什么,这样定义偏差太大。”何晓亮说:“我今天听他们说要设一百个名次,也就是前一百名是获奖鸽子,我们国内的鸽子能占到多少呢?”丁昊翔说:“这也很难说,首先我们不知道有多大比例的境外鸽,如果公棚收了两千羽鸽子,境外的只有三四十羽的话,那不用比我们就赢了。”
俩人正谈论着,丁胜男回来了。
她笑着换过拖鞋说:“爸爸,你们在谈论公棚?”
丁昊翔瞧瞧女儿说:“我们在闲聊呢。”
丁胜男挨着父亲坐下说:“爸爸,你觉得我妈办这个公棚究竟能不能行?”
丁昊翔说:“就看她怎么收费了,如果收费太高,恐怕不大好做。”
丁胜男说:“三百六十块钱一羽怎么样?”
丁昊祥微微闭上眼睛,摇着头,过了好一阵才说:“万事开头难,她得做好赔钱的思想准备。”
丁胜男说:“那你的意思是收费高了?”
丁昊翔说:“也不是说高,而是很多鸽友一时恐怕接受不了。”
何晓亮说:“收费绝对不能太低,如果为了多收鸽子,开始就把收费定得低了,以后再想提高就难得多了。你想想,做一个公棚,基础投资很大,不可能只做一次比赛,如果你今年为了吸引鸽友,定的是三百块钱一羽,而你明年涨到四百,他们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明年、后年甚至是将来的发展。”
丁昊祥说:“小何说的有一定道理,公棚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独门买卖,关键是让鸽友怎么认可它。”
丁胜男原本就对这件事情兴趣不大,而何晓亮与丁昊翔的话题越扯越远,不由得打了个哈欠。丁昊翔看了看她说:“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说过,他起身出了客厅。何晓亮也站了起来,丁胜男一边拾掇着茶几上的茶杯一边说:“有一个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何晓亮笑嘻嘻地看着她说:“什么差事?”
丁胜男见他的样子,有些生气地说:“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何晓亮的眼睛都快眯到一起了,他依旧笑着说:“我也没说你说的不是正经的呀。”
丁胜男负气道:“不跟你说了!”
何晓亮凑到近前说:“到底是什么差事?”
丁胜男说:“去把杯子洗了。”
何晓亮接过她手里茶盘单腿一弯说:“喳,奴才这就去。”
丁胜男噗嗤笑了,笑过后说:“你就‘贫’吧。”她边说边又从何晓亮的手里抢过茶盘去了厨房。何晓亮尾随着她来到厨房说:“到底是什么差事?”丁胜男说:“我妈想让你当公棚的经理。”听到这话,何晓亮愣了片刻,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手扶着门框久久地注视着丁胜男丰腴的后背。
丁胜男洗过茶盘回转身,猛然看到了何晓亮的眼神,她的心不由得嗵嗵地一阵跳。她稳了稳心神故作轻松地说:“嗨,你不上去睡觉等啥呢?”何晓亮的眼神热烈了,丁胜男的脸被那眼神炙烤得发烫,她低头侧身从他的身边正要挤过去,何晓亮揽住了她的腰,头也跟着凑过来。丁胜男的呼吸急促了,她又是兴奋又有些恐慌,在她不知所措中,何晓亮温热的嘴唇触到了她的耳唇。她挣扎着想脱出何晓亮的怀抱,可那双手如同铁箍一般,情急之下的丁胜男向后仰着身子用茶盘挡住了何晓亮的头。
茶盘被何晓亮撞斜了,上边的茶杯眼瞅着就要落地。何晓亮忙松开丁胜男去扶茶杯,借着这个空儿,丁胜男鱼一样滑出了何晓亮的怀抱。脱离开何晓亮的丁胜男眨了一下左眼,又冲父亲那边的房间努努嘴,然后伸出手指在脸上刮了刮脸。何晓亮被她那孩童似的动作迷住了,跨上一步,丁胜男作势欲逃。他停下脚步瞧着她神秘地笑了,丁胜男上下看看自己,没觉得哪里不妥,便问:“你笑什么?”何晓亮说:“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丁胜男歪着头想了想说:“不想说就拉倒,记着明天上午去找我妈。”
何晓亮依旧在笑。
丁胜男说:“别笑了,你到底愿不愿意接那差事?”
何晓亮点点头。
俩人从客厅里出来,何晓亮小声说:“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丁胜男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何晓亮说:“你还别说,真跟猪有联系。”丁胜男掐了他一把说:“快说!”何晓亮在她的耳边小声说:“我已经在你的耳朵上盖了章,你没见过从屠宰场里出来的猪肉都要盖一个蓝色的印章吗?记着,你的那个耳朵已经是我的了,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说过这话,他噔噔噔地上楼去了。
第二日上午,何晓亮去了荣思浓的家。荣思浓替他沏了杯茶说:“你想好了?”何晓亮点点头。荣思浓说:“我也不拿你当外人,选你做这个公棚经理并不全是胜男的缘故,我更看好你的能力。谈这件事情要抛开胜男,这样与你、与我都很公道。你在《南京赛鸽》的工资是每月六百元,我每月给你一千块,另外,到了年底给你提成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听到这里,何晓亮很激动,正要说话,荣思浓摆摆手说:“你先别急着说话,我的话还没有完。如果亏损了,你也要承担百分之十五。”
何晓亮有些着急,他心里想,这么大的投资,如果亏损了,他去哪儿找那许多的钱。荣思浓似乎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她说:“你也不用慌,这百分之十五可以挂到帐上,等明年或者后年有利润的时候,从你的收益中扣出来,你觉得这样行吗?”
何晓亮有些结巴地说:“荣老板、荣阿姨,你、你放心吧,难得您这么相信我,我会竭尽全力去做好这个公棚。”
荣思浓笑着说:“先别着急。还有一个需要跟你说清楚的事情,我们选的那块地是租来的,使用年限是三十年,地一共五十亩,每亩每年的租金是五十块,我前几天就把七万五千块钱给人家付了,这是合同,你看一看。”说着话,她把一份合同递给了何晓亮。何晓亮粗略地看了看,又把合同放到了桌子上。荣思浓说:“这里还有一份合同,是跟一家建筑公司签的,他们负责鸽舍及配套设施建设,包工包料,一共是四十七万,两项合计是五十四万五千元。我计划在五年之内收回这部分投资,也就是说,在计算利润的时候,每年要把这十万块打入到成本中,你明白吗?”
何晓亮点点头说:“我明白。”
荣思浓说:“你先回去仔细想一想,我找人草拟合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几天就把合同签了。”
3
四个月后,东方国际赛鸽公棚成立了。经过荣思浓、林云天等人多次的推敲,由何晓亮执笔的竞翔规程也定了出来。总奖金设了五十八万,前一百五十名都有奖,每羽鸽子的参赛费是三百八十元。冠军获奖八万、亚军获奖五万、季军获奖三万,四到十名的奖金是每羽八千元,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奖金是每羽六千元,二十一名到三十名的奖金是三千元,三十一名到一百名的奖金是两千元,一百零一名到一百五十名的奖金是每羽一千二百元。为了吸引有钱鸽友多交鸽子,何晓亮提议增设团体奖,奖励在一百五十名中获奖多的鸽友。团体奖的冠军获奖三万元,亚军获奖两万元,季军获奖一万元,四到五名是五千元。全部奖项设完后,还剩下四千元,何晓亮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五个幸运奖,这五个幸运奖分别是一百五十八名、一百六十八名、一百七十八名,一百八十八名和一百九十八名,每羽获奖八百元。
荣思浓最近比较窘迫,手头的资金有一百多万投入到了东方赛鸽公棚,另外的两百多万投到一笔钢材生意上。钱已经打给了张萧,可那边因车皮紧张,货迟迟发不过来。服装生意也相当清淡,几乎每天都在赔钱,迫不得已,她通过关系将自己的服装厂以及承包的荟城电子手表厂同时抵押给了银行,但一百二十万的贷款迟迟到不了位。那段日子,她满嘴燎泡,吃什么都没有味,体重整整降了二十斤。
到了四月初,她的状况非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倒越发地恶化了。东方赛鸽公棚那边也不太好,林云天的境外鸽子一羽也没到位,何晓亮动用了自己的各种关系,只收到了六百多羽鸽子。为了打开局面,荣思浓铤险挪用了东方赛鸽公棚十五万的收鸽款,又卖掉了自己的汽车。直到四月下旬,她又使了十万块钱,那批钢材才运到了荣城。接下来,她又用五万块钱打通了银行的关口,一百二十万的贷款也打到了自己的帐上。
挺过了这两个关口,荣思浓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
钢材的生意实在是太好了,仅这一笔,荣思浓就有了将近一百万的利润。第二笔钢材生意是在五月份启动的,她投入整整四百万,因为各种关系都已经打通,再加上张萧的斡旋,又有了近二百万的收入。也就在这时,欧洲、台湾、日本、美国的鸽子陆续进到了公棚。
截止到五月二十八日,东方赛鸽公棚收到国内的鸽子一千五百四十羽,境外的鸽子三百二十羽,两项合计一千八百六十羽。而此时的荣思浓已经不大在意公棚那边的情况了,她粗略地算了一下,自己设的奖金是五十八万,收到的鸽款已经快七十万了,已经有了几万块钱的利润。
这天,丁胜男忽然对她说:“妈,能让我爸往公棚里交点鸽子吗?”荣思浓沉吟了片刻说:“这是你爸的意思?”丁胜男摇了摇头说:“我爸没说,但他成天问我公棚那边的事情,我看得出他想在那里比赛。”荣思浓想了半晌才说:“你看过规程了吗?”丁胜男点了点头说:“看过了,规程中规定公棚内部的工作人员一概不允许以各种名义参加比赛。”说到这里,她停顿了片刻又说:“我爸又不是要作弊,那怕什么?”荣思浓摇头叹息道:“即便是我们不参加比赛,将来也难免有人说三道四,要是有了我们的鸽子,你想想会出现什么结果?”丁胜男见母亲作难,叹了口气说:“那就算了!”荣思浓把头靠在椅子背上迷了会眼睛说:“这样吧,你去跟晓亮商量一下,让他替你想想办法。”
自从公棚完工后,丁胜男只去过一次,乱哄哄的,几乎连个落脚地都没有,说句心里话,她实在不喜欢那地方。当她坐着母亲的新车再次来到那里时,真正吃了一惊。
正对着大门的是十几间鸽棚,鸽棚的颜色是淡黄色的,鸽棚的前面是大片的空场,围着空场的是低矮的女墙。空场两侧各有一条水泥路延伸到鸽棚前的那条甬道,里面不知种了什么,刚刚长出,看上去是浅浅淡淡的绿。空场前端是一片由水泥砖铺就的场地,鸽棚左右两侧是一长溜棚子,支撑棚子的柱子都涂成了红色,左边棚子的末端是六间房子,其中靠里边的一间的门上挂着经理室的牌子。
听到汽车的喇叭声,门房慌忙出来打开了大门,司机对这里很熟,径直将车开到经理室的门前。何晓亮正坐在办公室内沉思,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后,抬头向外看了看,见是荣思浓的汽车,忙起身迎了出去。车门打开后,丁胜男笑吟吟地走下来说:“没想到,真没想到你把这里拾掇得这么好。”何晓亮笑呵呵地说:“欢迎大小姐来指导工作。”丁胜男斜了他一眼说:“指导你个头!”
经理室是里外间,外间是一个宽敞的接待室,沿墙是一溜转角沙发和几张茶几,墙上悬挂着许多鸽子的大照片。办公桌正对着门,后面一个大大的皮椅,旁边有两盆高大的发财树。
丁胜男上下打量着房间说:“嘿,比我们科长的办公室还豪华。”这样说着,她推开了里间的门,何晓亮跟着进来忽然从后面搂住了她的腰。丁胜男小声说:“快松开,看叫司机看见的。”何晓亮非但没有松开,反而搂得更紧了,他的脚将身后的门勾了回来。丁胜男侧仰着脸说:“你要是这样,我下次可就不……”她的话还没说完,嘴唇已经被何晓亮吻住了。
良久,丁胜男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绯红着脸说:“别闹了,我有正经事跟你商量。”两人重新回到外间,何晓亮给丁胜男沏了茶水说:“啥事?”丁胜男就把父亲想参加比赛又不好开口的事情说了一遍。
何晓亮稍稍思索了片刻说:“那你妈知道这事吗?”
丁胜男说:“我妈挺作难,让我找你想个办法。”
何晓亮说:“我记得你爸爸给内蒙的亲戚孵了一批幼鸽,不知道你家的那亲戚有没有取走鸽子。”
丁胜男说:“好像还没有,前天还听他念叨是要托一个跑内蒙的列车员给人家送过去呢。”
何晓亮说:“那你赶紧回家,别让你爸爸发鸽子,我知道那批鸽子的质量很好,它们佩带的还是内蒙的足环,你只需要换一个别人不晓得的名字交来就行了。这样,一来免去了许多瓜田李下的嫌疑,另一方面,即便你爸爸的鸽子在这里表现不好,也不会影响到他在鸽界的声誉。”
丁胜男笑着说:“没怎么着呢,就要撵我走,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怕我知道?”何晓亮涎着脸凑过来,丁胜男忙躲到一边说:“别说话,狗嘴里准吐不出象牙。”何晓亮还准备腻味一会儿,外面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他起身向窗外看了看,见两个年轻人提着一个小笼子走了过来。他忙说:“有交鸽子的了,你什么也别说,抓紧时间回家去取鸽子,晚上过来,我等你。”说这话时,他坏坏地瞧着她,用手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
丁胜男站起身狠狠拧了他一把,小声说:“你就缺德吧。”
从公棚里出来,丁胜男回味着刚才的情节,想着晚上过来能发生什么,想着想着,她的两颊便腾起了两朵红云。正发着呆,司机问:“胜男,我们现在去哪里?”丁胜男愣了一下才说:“把我送回家。”
进了家门,爸爸不在屋子里,她转身上了楼顶,见爸爸正在鸽棚里给一个唧唧叫的小鸽子塞药。她大声说:“爸爸,你给内蒙亲戚孵的鸽子发走了吗?”丁昊翔抬起头疑惑地看了看她说:“你怎么知道我给别人孵了鸽子?”丁胜男说:“那你就别管了,那些鸽子我要了。”
丁昊翔放下手里的鸽子说:“你要那些鸽子干什么?”
丁胜男说:“我就不能参加比赛吗?”
听到她的话,丁昊翔微微地笑着说:“胜男,爸爸知道你的意思,爸爸也真想跟那些外国人见个高低,但咱们不能那么做,凡事都要有个规矩。”
丁胜男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们又不是要作弊,凭啥偏偏是我们的鸽子不能送过去比赛?”
丁昊翔从鸽棚里出来说:“走吧,咱们下去吧,爸爸已经把鱼给你炖好了。”丁胜男还要坚持,但看到父亲的神态,知道坚持也没用,只好跟着他从楼顶下来。
吃过饭,丁胜男又缠了爸爸很久,可他就是不同意。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给何晓亮打电话说了这件事,何晓亮戏谑道:“你真是个猪头,一会找个机会偷着把鸽子送过来就是了。”
电话这边丁胜男啪地敲了自己的脑袋一下说:“我可真够笨!”何晓亮哈哈笑着说:“轻点,我会心疼的。”丁胜男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敲自己的脑袋了?”何晓亮说:“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下午,趁着丁昊翔午睡时,丁胜男上楼顶去挑鸽子。令她头痛的是,小鸽子实在太多了,找了半天,只找到六个佩带内蒙足环的鸽子。傍晚时,她偷偷地拿着鸽子打了个车去了公棚。
在填写参赛卡时,何晓亮说:“用什么名字?”丁胜男歪着头想了想说:“我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就用丁晓这个名字参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