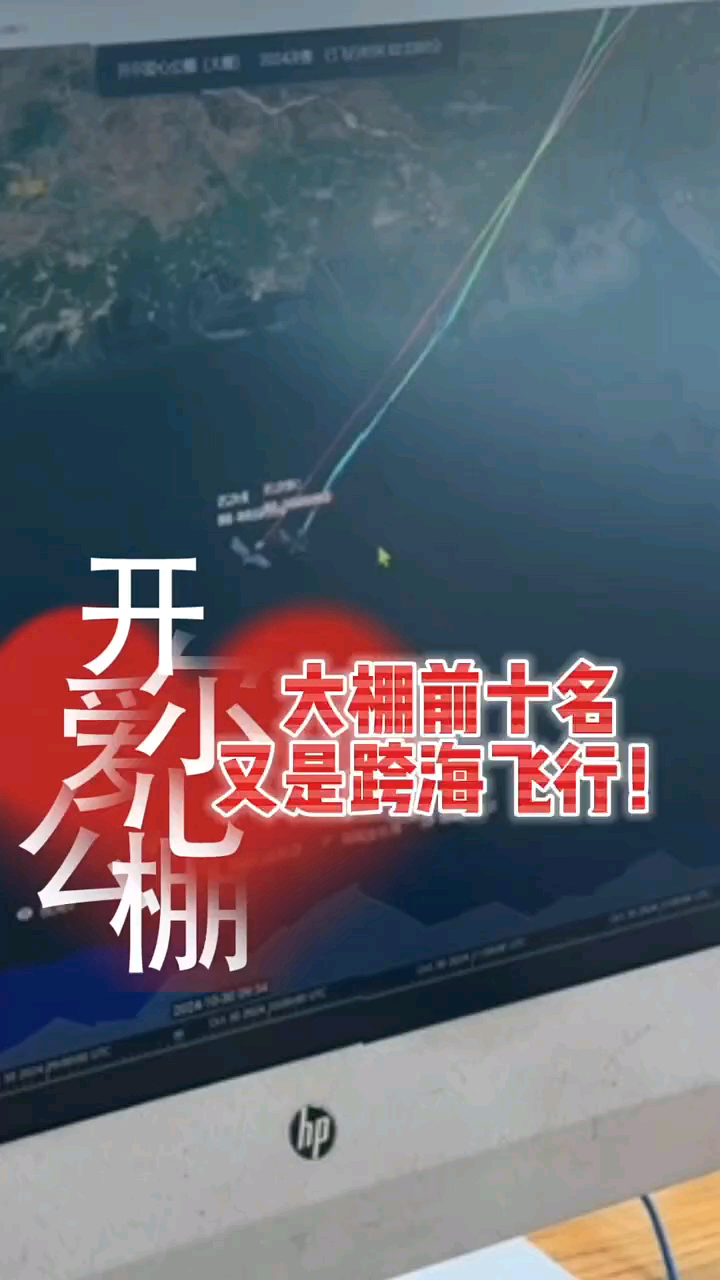去年年底,老妈去世,我回家奔丧,又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老院子。在晨练时竟然发现,在这片即将拆除的旧楼群里,在我们40年前养鸽子的凉台上,竟然还有人在养鸽子。这使我感慨万分,回忆起小时候养鸽子的故事。
40年前的中国,全国上下出现过一段无法无天的真空期。在这期间,各地的派系之间发生了各种规模的械斗。听武汉百万雄师(被伟人利用时是革命组织,利用完了就变成反动组织)的哥们儿说,在当时的武汉,在大街上打枪就像过节时放炮一样随便。出门上街时,他妈妈不是像北京的妈妈们给孩子一点零花钱,车马费什么的,而是从菜篮子里掏出两颗手榴弹,并嘱咐他上街要小心防范。那时候武汉的孩子们都练就了一双飞毛腿,并号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甩上两颗手榴弹就赶紧闪了。文革是成年人的地狱,孩子们的天堂。那时的人命真不值几个钱。哪像现在呀,被人打个嘴巴,被人骂上一顿都得上法院,动不动就诉讼一把。
但好景不长,突然,一夜之间,过去的革命精英又变成了反革命,青年人的革命热情被一盆冷水彻底扑灭。大学生们开始各奔前程,中学生们整天无所事事,就在这段时间在京城的孩子们想起了养鸽子。那时候的中国人的家里除了家禽和兔子,可养的宠物确实不多。
40年前的京城,楼群里几乎没有养鸽子的,如果有也是几千分之一。传统的养鸽人都生活在老城区的胡同里。但这两拨孩子是老死不相往来。从哪可以搞到鸽子呢?鸽子市?买?按当时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家里每天顶多只给孩子一两毛钱。在鸽子市上看得上眼的鸽子也要十块钱一对,二三十元的也有,五十元的是凤毛羚角。靠攒钱买鸽子看来太慢了。于是,楼里的孩子们开始对鸽子市产生了兴趣,动起了坏主意。先给它扣上一顶四旧的帽子,再给它加上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就为下一步的行动打好了舆论基础。
京城的鸽子市历史悠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也没有停止过,政府也认为它是投机倒把,是伟大首都的黑暗角落,一直查抄不断。所以抄鸽子市还被套上了替天行道的光环。
于是鸽子市上的紧急警报声发生了变化,从抄鸽子的来了!(抄鸽子北京话的意思就是抢鸽子,像现在的城管抄路边小贩。)变成了“联动”来抄鸽子了!(联动是文革初期北京学生中自认为革命血统最纯正的学生组织,后来的反动组织。)警报声频频响起,鸽子市立马成了彩鸽市。其实哪里是什么联动,充其量就是几个联动残余带着一帮楼群里孩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嘴里喊着替天行道,行的却是砸明火的勾当。40十年前,在京城两拨完全对立的超级鸽迷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传统的和入侵者打得头破血流。
鸽子市的行动虽然壮观,但收获不会很大。你一冲锋,人家就把彩鸽放了。收获的很可能是一堆老玉米豆。那时候的老玉米豆才五分钱一斤,三来二去,楼群里的鸽迷开始把目标定在平房区的养鸽人身上了。
那个年代抄家如儿戏,想抄谁家就抄谁家。抄家的名目也繁多,有抄黑材料的,有抄四旧的,现在的马为都要搁那会儿,八成也变成马连良了。那叫无法无天!令人发指!近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翻了个底朝天。
话说这联动在鸽子市上收获不大,就去搜索平房区。先是尖兵出动侦察,这一侦察可不要紧。原来这四九城儿的平房区里墩着大量的好鸽子,土匪们发现了真正的宝库。我黑龙江兵团的同班战友姜民生就是那时平房区的养鸽精英。几天前他还给我打电话臭显摆,说又花了三百万买了几只比利时鸽子。最贵的一只60万。这老家伙强烈邀请我去参观,我说你就不怕我顺你俩鸽子蛋?大姜大笑道:“他妈的,咱俩谁跟谁呀!”大姜和我同在一个班养鹿,后来他又去酿酒。结果把自己的胃喝了个胃穿孔,他是我认识的最疯狂的鸽痴。以后有时间我一定的写一篇大姜的故事。我一聊起来就跑题,咱赶紧调头。
于是攻击准备就开始了。先纠集人马,是部队的不是部队的都穿着一身黄皮。骑着当时最牛*的自行车,背着军用挎包,里面装刀子板儿砖之类。他们的基本战术就是呐喊加板儿砖,按现在的话叫先把他拍呼住。如果遇见鸽主悚了,他们就冲进门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是直奔鸽子窝,抢了鸽子就走。这叫“端”鸽子(明明是抢鸽子他就是不说抢,他管这叫端)。“端”了人家鸽子之后,还不忘撂下几句破四旧的狠话。
“端”鸽子的初期,这种行为还能拍呼主人。但到了后来楼群里的孩子们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渐渐知道了平房区鸽迷们的厉害。
一天我和几个朋友正在院里闲聊,忽见一哨人马漂进了院里。为首的是包大嘴,包大嘴在院里可不是等闲之辈,论血统跟谁都有一拼。他老爸在1921年7月1日,就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坐在一个桌上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我们这帮孩子都是包老头的拥趸,因为他的知识太渊博,故事特别多。听他讲起陈独秀来那叫眉飞色舞,那是他年轻时的偶像,他对伟大领袖的印象不深,好像他在会上就没咋说话。他可懂得什么叫黑白两道,戴笠当时多牛呀,也没把他怎么样,他满脑袋都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他忆往昔的时候,脑门子都发光。
包大嘴一进院就嚷嚷开了:“今天可碰上硬茬口了。咱一阵板儿砖过后,不但没把人砸趴下。嘿!反倒从门里砸出四条大汉。这四条汉子每人手中一杆长矛,我*他妈的!咱乌合之众遇上遇上练武的了。我们四十多黄皮子,扔了第二阵板儿砖之后,撒腿就跑了!连第三条腿都用上了!”血统啊!血统!血统太重要了!有包老头的遗传垫底,包大嘴能不跑吗!跑了就对了,不然,哪还有现在的资本家包大嘴呢?
要说打架斗狠。北京人永远比不过东北,内蒙和湖北人。俗话说得好,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人家是说干就干,而且是干倒了算。北京人不是这样的,北京人是说干不干,等待中间人出现,然后是几经套瓷就化干戈为玉帛了。看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就明白那段历史了。
后来新的《公检法》确立,这种事情就销声匿迹了。楼群里的孩子和胡同里的孩子也有了一定的交流,楼群里的鸽子也就多了起来。
鸽子是有了,可养鸽子,养好鸽子的经费又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那一帮13、4岁的小孩子,家里没爹没妈,每天的零花钱都没着落。拿什么养鸽子呢?我们开始变卖家产。那时候的家里哪有什么家产,就是有书,上世纪30年代咱老爸就是个读书人,一直搞地下工作,事发前,小官做到县里的税务局长。那时候月薪200块大洋,到了新四军以后他兜里的大洋还叮当响。他一时间成了部队里的有钱人,他没有别的嗜好,一不吸烟,二不喝酒,就爱看书,买书。解放后他就变成了琉璃厂的常客,所以我们家里除了书就是书。
卖书吧!几个小哥们儿帮忙,一回就把我老爸积攒了一辈子的书全卖了。我还记得卖书的时候,旁边有一位老者,一边看,一边嘬牙花子:“太可惜了,这样的书怎么能卖呢!怎么能卖呢!”老书迷碰上了小鸽迷就像秀才遇上了兵,那么好的线装书都变成了造纸原料,到现在我都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感到内疚,可老爸竟然一句也没骂我。又拐弯了,赶紧刹车。卖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小伙伴们忽然发现右安门鸽子市的旁边有一间国营的土畜产收购站。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国家,为了增加一些营养,几乎每个城市家庭都养有家禽和兔子之类的东西。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干,家里都种自留地,多余的产品可以出售给国家开收购站。兔子是五毛钱一斤,哇噻!找兔子去吧!于是,从铁道部到华北局再到广播局(当然自己大院里的也不能放过)方圆几里地,几乎所有在一楼养兔子的家庭都遭了殃。瓦西里好像也说过:“粮食会有的,鸽子也会有的。”可各家的兔子却没有了。
去年的发小大聚会上,50多岁的吕菜货正眉飞色舞的侃着这段光荣的养鸽历史之即。忽听“啪”的一声巨响,一个小胖子拍案而起。我*!原来是房地产大亨于扁宽!走样了!走样了!小时候的于扁宽,那叫一个英俊,处女们排着队跟他发生一夜情都不觉得后悔。据说这小子在炮局里都能勾搭上漂亮女犯人。他是我的发小,也是我的猎友,以后有时间我一定给大家讲讲我们打猎的故事。
再说于扁宽拍案而起:“哈哈!老三呀老三!我今天才知道,我们家40年前大兔子失窃案的主犯是你!我妹妹为了那十几斤的大兔子哭了足足一礼拜!”他妹妹小荣和我在幼儿园是同班,中学又是同学。惭愧呀惭愧!现在一想起儿时的糗事,真有没脸见江东父老的感觉。扁宽他爸是个老红军,早早就被收监了。我们俩穷的时候,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互相接济。
疯狂的时代塑造了一批疯狂的鸽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穷则思变。一群贫穷的毛孩子按照主席的教导办点事怎么就那么难!你能想象那帮局长副局长,部长副部长的家属们和国民党参事们看守着自己家的劳动果实,甚至守到下半夜三点半有多辛苦吗?疯狂的小鸽迷们是根本想不到的。因为他们行动的时间是下半夜4点。哈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
吕菜货随笔

|
中信网
|

|
|
手机版 中信网 |
| 在线铭鸽展售 |
| 鸽具饲料展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