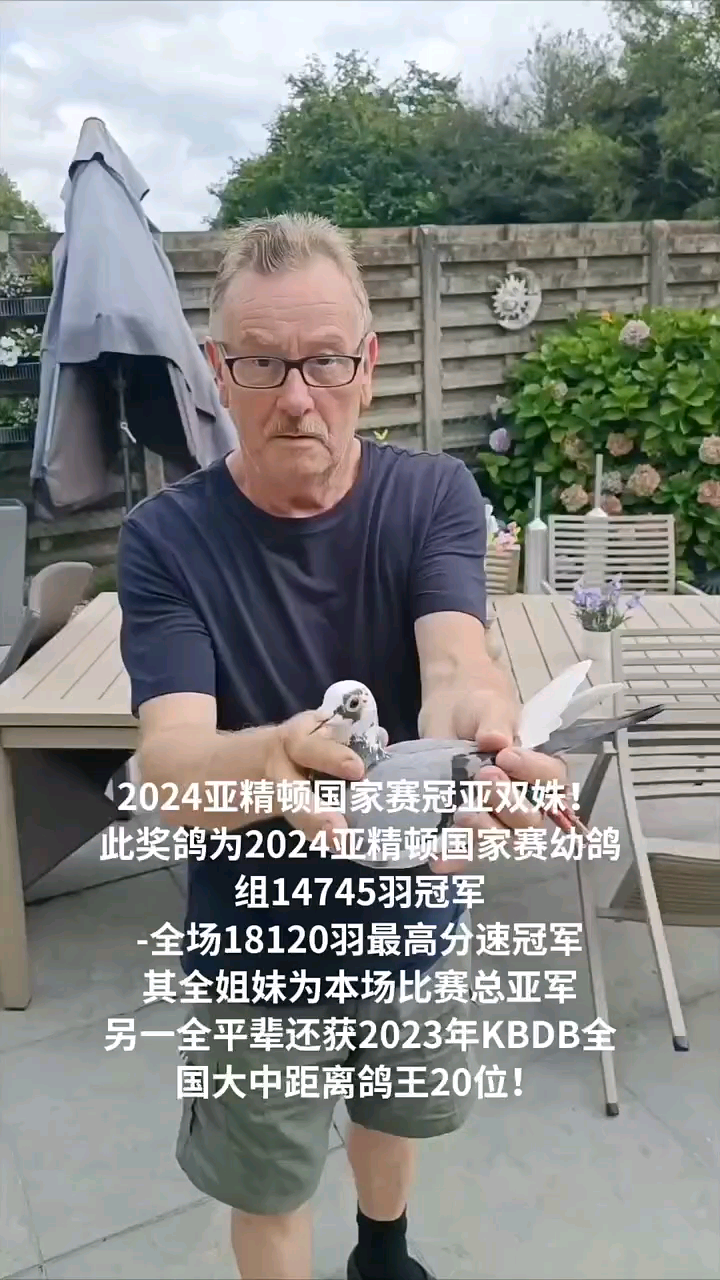永远的情怀
——致张顺奎老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顺奎老先生:
您好!
我是一个69年带着鸽子去云南插队的六七届上海老知青。虽然此身屡遭罹难坎坷,养鸽断断续续,但对鸽子的挚爱和研究却有着一生不灭的情怀。现在退休回原籍,闲下来则在网上建了一个自己的专栏,只是想说说鸽子,也许这就是对信鸽这个令人着迷的尤物依然恋恋不舍的原因吧。
有意在网上拜读了你的专栏文章,感触很深。你们“老二代”前辈在文革中对中国的信鸽事业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你们在危难中保护和发扬光大了我国的信鸽事业,你们的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感动着我至今。
先生,你是个十分谦虚的人。我是早年通过你的云南挚友了解到你,但你并不认识我。看了你的专栏,我感动的同时也深感遗憾。在这里我想为您,不!是为中国的信鸽史,为我们上海的信鸽事业,你和老一辈曾经所作的贡献,说几句真实感言。
你在专栏里发表的所有文章,唯一让我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没有一篇提及当年云南军鸽与上海渊源的这段真实历史,这一定是你谦虚的原因。你当时作为上海信鸽协会的领导,积极支援石宝铨、陈文广率领云南军鸽队在上海进行军用鸽征招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这批征招的“信鸽兵”,对后来云南军鸽和民鸽的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云南之所以能在七十年代末就成为赛鸽大省,究其渊源,是和这段信鸽征兵史是分不开的。云南军用鸽在300公里以内高原山地集训全归,靠它们的血统。云南信鸽突破千公里也靠它们的血统。当年你的十一条、毛脚雌、汪老的西安冠军、秀龙的西宁九名、丁陪新的飞轮,还有白砂雌、三五雄、马鞍山雄等等一大批上海当年优秀种鸽,在80年以后频繁的机会里,无论在军鸽队和民间的,我几乎对它们全有过深度接触,印象颇深。它们的后代在民间有梅金昌的武汉冠军、石宝铨的长沙冠军,以及您的十一条后代(种鸽石宝铨支援)在云南烟草之乡玉溪也飞出了长沙。
在军鸽队,记得80年放12只上海,有一只深雨点砂眼雌,伯马飞回昆明关上军鸽场,这只鸽子的归巢真实性在民间至今一直众说纷纭。当年我第一次在昆明军鸽队举办的信鸽展览中曾见过这羽鸽子,后来又在一次参观军鸽场时也上过手。陈文广先生是个很好客的军人,当听到身边一起长大的至亲鸽友(我的已故挚友)向他介绍,我是个在云南工作的上海鸽友时,就额外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同时让我得到了上手上海鸽这个特殊待遇。我从小喜欢专于研究信鸽种性,尤其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给了我机会,对上海老一辈优秀种鸽的了解,至今仍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说句老实话,我认为那只鸽子是真的!我也赞成这样猜测:它极可能就是你老太原血统里的深雨点李种(也许是十一条血统),和蔡老先生当年推荐征兵的一只多次放过1000公里记录的砂眼吴淞雌的直子。社会上虽然有不同说法,然凭我个人经验却还是这么认为。
我其实很理解云南军鸽队,我认为作为培养军鸽,陈文广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用上海的优秀品系,和适应云南高原山地飞行的高原种系杂交,育出了一代500公里以内(特别是300公里)极其稳定、不怕风雨,又能与人亲和、听人指挥的新鸽兵,改良了老高原品系,提高了它们的距离和速度档次,对当年部队军鸽在战时适用上的好处也是无可非议的。听说他为此曾得到过部队嘉奖,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很理解广大鸽友在以后30年,竟然再没有第二羽从上海飞回云南的困惑。这需要我们的突破,就像八十年代从长沙飞回第一只9名红绛,打破了红绛在云南不可能从千公里飞回的断言,而且它就是一只八五年从上海引进的孟源红绛直子。
从历史的客观角度看,当年云南部队在上海征鸽,没有陈文广主动向上级打报告不行,没有您领导的上海信鸽协会的大力支持也不行。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由于信鸽的国家征用,使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养鸽家,在那个浩劫的年代里终止了吴桂桢的鸽棚悲剧,得到了名正言顺的保护。这一点您老当年领导的上海鸽协也是作出贡献的,我们都不应忘记那段历史。
有人曾建议我写当年上海种鸽从军云南军鸽队的故事,我想只有您才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你和那些上海老一辈养鸽家才是那个时代的当事人、见证人。想当年,你来昆明考察军鸽,和云南朋友一起游览昆明西山,讨论传授养鸽经验,那可真是一幕很难忘的轶事……
由衷的希望您老,能为我们广大鸽友揭开这光荣的一幕历史。
最后祝您老身体健康,快乐长寿。
虞海明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