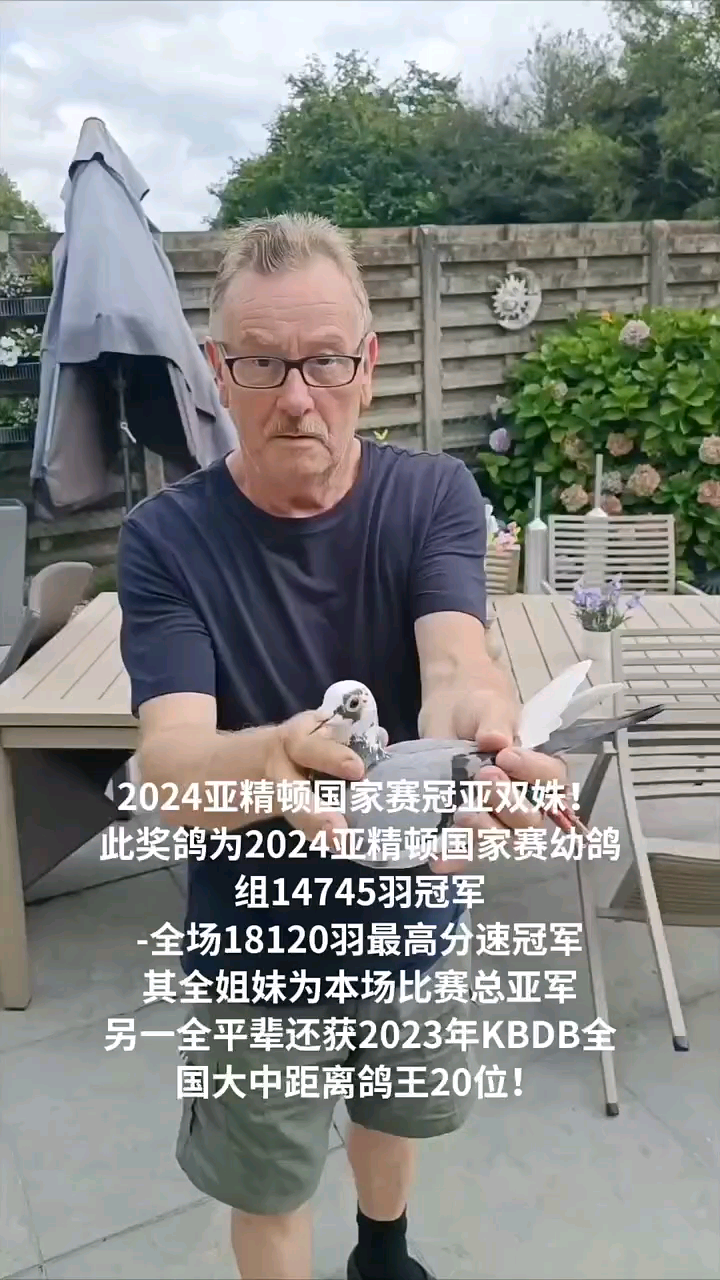消亡
长篇小说
回眸我国七十年的赛鸽运动,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需要引进,但我们更需要反思。
透过赛鸽的本质,是中西文化的两次碰撞,结果又如何?
国内文学史上第一部赛鸽类长篇小说——
上篇
1 荣城的清晨
1
荣城的清晨总是从那一望无际的屋脊边缘处喷涌而出。薄雾淡去,浩瀚的屋脊上便飘渺起缕缕青烟,或直、或弯,或淡得与天融为一色、或浓得犹如卷起的旋风。清风微拂,扯动雾霭,北边的楼台宫阙、苍松翠柏便清晰、苍翠起来。
海棠初后,杨柳浓时。
天气格外的晴朗,空气中散发着丁香的清香。微风掠过,香味时而淡然绵长,时而浓郁如酒。三两树玫瑰的枝头孕育了小巧的花蕾,还没有到开放的时节,倒是满架的紫藤花绒球一般,在嫩黄的叶片下,一串串倒垂着。这些当然是在一个算不上显赫的院落里。与荣城其他的院落相比,这个院落东侧的小花园里多了一间房子,房子正面罩着铁网,如同公园里关孔雀或是鹦鹉的那种笼子。
青年丁一凡左手持一小铲,右手拿一笤帚,在房子里专心致志地清扫着一排排巢格。阳光透过铁网射了进来,地上便斑驳起三尺见方的影子,一些漂浮着的粉状碎屑被一道道横七竖八的光柱搅得沸沸扬扬。
地上的光影细成窄窄的一条时,丁一凡便推开阁楼的小门,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抹抹鼻翼间细微的汗珠,脱掉身上那件白大褂啪啪地抖落几下。稍倾,大群颜色灰白的鸽子沙沙地掠过头顶。
这时,精瘦的李妈踮着小脚越过东北角的月亮门,手搭凉棚站在紫藤花架下喊道:“少爷,开饭啦。”她的尾音拖得很长且韵味十足。透过那悠长的尾音,江南的小桥、流水便氤氲成淡然的哀伤盈满心间。
丁一凡走出那间房子,转过月亮门,进屋净罢手。李妈把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和一块焦黄面包放在矮几上。他端起牛奶轻轻呷了一口,眉头蹙紧。旁边的李妈道:“少爷,是不是太烫了?”丁一凡摇头道:“不碍事,你先下去吧。”李妈知趣地转身,她太了解丁家老少的脾气了,少爷哪儿都不像老爷,惟独这吃饭不喜欢别人打搅随了老爷。
将出了上房的门,砰砰的敲门声响起,她踮着双小脚紧走几步道:“来了,来了。”转过内院,打开大门,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者个头不高,眼睛狭长,扣在头上的巴拿马帽下是一条颜色紫红的疤痕,斜插入鬓。穿一件蓝绸布汗衫,横腰系一条大板带,板带上缀着一个鼻烟壶和几个小饰物,白绸布裤。李妈迟疑间,那人从李妈身旁挤了进来。李妈道:“你这位爷,你是找谁呀?”
那人道:“不找谁,我看到我的白大鼻子落到了你家的房顶上。”说话工夫,他钻过月亮门跃上了左边的矮墙,抻着脖子踮着脚,两只眼睛叽里咕噜地瞧向鸽棚。
听得响动,丁一凡踏出门槛转到月亮门口道:“先生,你这是做什么?”那人看到丁一凡,麻利地从墙头上跃下来道:“你是新搬来的?面生得很,我的白大鼻子落到了你家,我能上去看看吗?”
丁一凡见他装束,无疑是个破落户,冷冷道:“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再说,我刚刚打扫完鸽棚,别说你的白大鼻子,就是我的鸽子都还没有回来,没什么事,先生请便吧。”
见丁一凡恼了,那人道:“这位爷莫要生气,那白大鼻子是我用两个鼻烟壶才换来的,少了它,我家里那个白大鼻子就没了老婆,孤单得厉害,我也会睡不着觉的。”
丁一凡听他说的俏皮,火气消了大半,他笑道:“先生贵姓,家居何处?”那人道:“免贵姓荣,人称荣三爷的便是我,住的离这里不远,隔两条街,贝勒胡同的荣宅。”丁一凡暗自道,果然是个破落子弟。贝勒胡同当年在荣城有相当的名气,他们祖上都是些达官显贵,这些子弟往往刁钻蛮横,不好相与。再者,漫说他的白大鼻子不在这里,就是在他也看不上的。既是如此,何不让他仔细瞧瞧,免得犯这嫌疑。
想到此处,丁一凡道:“原来是荣三爷,久仰,久仰。请跟我过来看吧。”说罢,他领着荣三爷转到那鸽棚前。此时,丁一凡的鸽子都已经落下,房子上下咕噜噜的叫声响成一片。荣三爷左瞅瞅、右看看,却没有发现他的白大鼻子。他扯下巴拿马帽不停地扇着道:“先生来荣城不久吧,怎么称呼呢?”丁一凡道:“免贵姓丁,丁一凡。”荣三爷笑道:“先生是南边来的?这些鸽子可不如先生,假如先生得了闲暇,改日到鄙宅看看,打扰先生了。”说罢,大剌剌地出了角门,一摇三晃地离去。
瞅着他的背影,丁一凡鄙夷地撇撇嘴。
2
太阳变小了,扯掉面纱的屋脊裸露丑陋的面孔,朝西越过两条街,可以真切地看到西区的房屋。门镂空雕花有着尖尖的角,夹竹桃跳动着跃出墙外,红灿灿的,小巧的阳台,教堂般的屋顶。那里是租界,是外国人住的地方,荣城鸽会就在里面。丁一凡很是向往那个地方,也非常想加入到里面,但从未去过,因为那个名为荣城鸽会的组织里没有一个华人。听朋友说,并不是华人不愿意参加,而是他们瞧不起华人,说华人养鸽水准低,没有资格参加。滑天下之大稽,名曰荣城鸽会,鸽会却没有一个华人,还叫什么荣城鸽会!转念又想到刚离去的荣三爷,愤愤中平添了些黯然。在荣城,荣三爷这类子弟太多了,而他们又代表着荣城鸽界的流向。他也想不明白,在德国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并没有太过于歧视华人留学生,谁知回到国内,却是这般境况。他曾不止一次发誓要教训一下那群狂妄的家伙。
沉吟间,李妈喊:“少爷,朱小姐来了。”丁一凡从屋顶上下来,李妈端上白洋瓷盆。盆里的水散发着热气,丁一凡白皙秀气的十指在水中微微弯曲、伸展。片刻,李妈将搭在盆架上的毛巾递上。丁一凡将毛巾折得方方正正蒙在脸上,贪婪地吸食着毛巾上的潮气。毛巾渐冷,李妈捧出一件领子浆洗得硬硬的白衬衣。丁一凡穿上衬衣缓缓打好领带,一双泛着亮光的皮鞋便在脚下。
每到这时,他会想起他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走出多远,自己这个留洋博士的血脉里依旧流淌着祖辈们的血液。他尝试着扯断、割裂,但那点东西却偏偏淡然悠长、绵绵不绝。它好比一条平静的小溪,没有狂风暴雨,没有惊涛骇浪,遇到开阔的河道,它会随意舒展开来;遇到窄小的罅隙,它变换一种形状;遇到荒沙野地,它便细小起来,但它永远不会消失。
跨过右侧的月亮门,丁一凡便换作了另外一个人,白大褂、白帽子、面色祥和、目光深邃、步履快捷却又不张狂。月亮门外的小院落整洁干净,两树丁香芬芳吐艳,几枝不甘寂寞的紫藤越过矮墙。院子的一侧停着一辆洋车,车夫肩上搭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蹲在墙根吸烟纳凉。朱秀云小姐俏生生地站在丁香树下,轻摇着一块手帕。她的头稍稍高出丁香几分,紫白色的花朵衬托下,脸颊越发显得娇艳
丁一凡不由得笑着赞了声:“人面桃花哟!”朱秀云的脸上飘过一抹红晕,她浅浅地笑着道:“丁博士说笑了。”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响起,“他说笑了?他怎么会说笑呢?他这是巴结你,当心上了他的当!”随着话音,门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穿着印花亮纱旗衫的女孩,她手里捏着一个细梗草帽,妩媚端正的圆脸上嵌着一对浅浅的酒窝,与朱秀云小姐相比,她的眼睛不是顶大,可是灵活温柔,使人一见就难以忘怀。
丁一凡侧脸看去,却是林紫烟。林小姐跳着从台阶上下来道:“老侄儿,难道我说的不对?”朱小姐脸色酡红,她啐道:“当心你的嘴长蛆的,乱嚼舌根子。”林紫烟仿着丁一凡的声音说:“人面桃花呀!”接着又捏着嗓子说,“丁博士说笑了。”说罢,跳着跑向屋子里。丁一凡尴尬地笑着道:“朱小姐,请进,小孩子顽皮,不必理她的。”
林小姐听到丁一凡的话,鼓着腮又跳出来道:“我是小孩子,那你是什么?你难道不是我的侄儿吗?再者,你这么说原本就不对,摆明了是生分我和朱小姐,你认识她才几天,若不是我,你怎会认识她呢!”丁一凡叹了口气说:“紫烟,我的小表姑,我的姑奶奶,你不是小孩子总行了吧。”林紫烟把手中的草帽向桌上一摔,道:“表姑就是表姑,怎么还得加个小字呢?我不理你们啦。”说着便去戏弄缸里的几条金鱼。逗弄了一番,金鱼都沉到缸底。林小姐抓着草帽晃来晃去,就像一只淘气的猫在晃动它的尾巴。冷不丁,她一把扯下墙角的一块白布嘀咕道:“总是不让我看,我倒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随着她的话音,一个橡胶人体模型出现了。林小姐的脸腾地红了,她忙上前遮盖并啐道:“这么个丑东西,比麦克修家那个缺胳膊的石膏像还难看。”丁一凡斥道:“紫烟,你太顽皮了!”听到这边吵闹,刘看护从里间出来道:“林小姐,我有话对你说。”一边说着话,她麻利地把人体模型露着半截的身子盖好,扯了林紫嫣出去了。
丁一凡挂上听脉器示意朱小姐坐下,朱秀云顺从地坐在丁一凡的对面,百无聊赖地玩弄着桌上的一只自来水笔,郁郁寡欢的样子。丁一凡的食指轻轻扣击着桌面。林紫烟出门那一刻,扭转头做了个鬼脸道:“我们出去了,你们可不许……”说话时,她的眼神中透出几丝捉黠的笑意。丁一凡没有理会她,他的十指停顿在光滑的桌面上道:“朱小姐,你的头痛属于神经性的,你愿不愿意试试中医的疗法?”
朱小姐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道:“丁博士,你说什么?”丁一凡道:“我想用中医的疗法治你的头痛会有相当的效果。”朱小姐的眉头皱成一团道:“我见不得中药,那黑糊糊的药汤让我恶心。”丁一凡笑道:“中医也不全是喝汤药的,我说的是针灸。”朱小姐疑惑道:“你这个留洋博士怎么会针灸呢?”丁一凡悠然道:“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祖父是江南有名的中医,小时侯他常教导我,不为名相,便为名医。”
门口传出轻微的咳嗽声,稍后,门帘呼哒被掀起,李妈轻手轻脚地走到丁一凡身旁小声道:“少爷,门外先后来了几个人,鬼头鬼脑的,不知要做些什么?”丁一凡一愣,恰在此时,林紫烟在外边喝道:“你们探头探脑地要干什么?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地进来办?”听到声音,丁一凡对朱秀云说,“朱小姐,你稍候,我马上就回来。”他三步跨做两步出了大门,看到的只是两个远去的背影。见他犹疑的表情,朱小姐担心道:“丁博士,要不要让我父亲给你找两个巡捕过来?”
丁一凡微微一笑道:“不必麻烦令尊大人了,不会有什么事的,还是谈我们刚才的话题吧,看你有没有勇气试试针灸?”
朱小姐抿紧嘴唇用力点点头。丁一凡从柜中取出一个淡黄色的旧包裹,打开包裹,里面是几层白色稠布,稠布的里面是十几枚银针。朱小姐吃惊瞪着那些银针,细的如牛毛,粗的似麦芒。丁一凡缓缓道:“朱小姐家居西区,不知令尊大人与西区的洋人有无来往?”这话既无意又有意,说它无意,则是为了分散朱小姐的注意力,免得她恐慌;说它有意,丁一凡可是考虑了好长时间,他想借助朱小姐家的声望进入荣城鸽会。
朱小姐早知他想加入到洋人办的一个鸽会里。此时,她却只在留意丁一凡的手。那双手修长、干燥,触到她的额头,丝丝热气便由表及里,熨贴得很。她的心一荡,眼帘微垂,鼻翼间沁出细细的汗。丁一凡以为她是紧张,插科打诨道:“朱小姐的肌肤真好,真是弹指欲破,我都不忍心下针了。”嘴上说着,手中的银针行云流水般布在朱小姐的头上。
朱秀云低垂的睫毛颤动着,眼皮轻轻一跳道:“家父与他们是赛马场上的朋友,早些年他在衙门里做事的时候,就相识的。”丁一凡正待说什么,林紫烟提了一根白棉线,下面挂了一个草绿色的大蜻蜓,笑嘻嘻地走了进来道:“你们俩个说完没有?我可是要回去了。”丁一凡道:“再等一会子,我起了朱小姐头上的针就没事了。”
林紫烟走到朱秀云的近前,左右前后仔细地查看着她头上的针。朱秀云瞅着她手中的蜻蜓不住气地说:“紫烟,快把那东西拿远些,我见不得这些小虫物。”林紫烟却把手中的棉线摇了几下,那蜻蜓的翅膀呼扇着发出轻微的响动。因怕头上的针,她不敢动,只是眼巴巴地瞅着风车般转动的蜻蜓道:“紫烟,你再耍笑,晚上的跳舞会就不叫你了。”林紫烟歪着头瞪圆了眼似不信,她自言自语道:“你又在冤我。”说着话,她的手一松,那蜻蜓拖着根棉线飞向窗子,“砰”地一声撞到玻璃上。丁一凡过去将窗子打开,蜻蜓歪歪斜斜地飞了出去。
看着出窗外的蜻蜓,林紫烟道:“好端端地开什么跳舞会?” 朱秀云道:“我的表妹前些日子从欧洲回来小住些日子,她吵闹着要开个跳舞会,舅父怕她气闷,就同意了。丁博士,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呀?”丁一凡顿了片刻,他想自己与朱家不大熟悉,以什么身份去呢?若是朱小姐引见,势必会让别人猜疑他是朱小姐的朋友,在这样的交际场如此亮相,未免有些唐突。曾听表嫂说起过朱小姐的情形,嫁过去三天就死了丈夫,回转家又患了一场大病。他很同情她的遭遇,又喜她善解人意,来往的日子久了,这种同情中又搀杂了些淡淡的情愫。犹豫间,林紫烟道:“他怎么会不去呢?他若是不去不就白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思,把我瞒得死死的,却先请他,莫不是你来的目的就是请他参加跳舞会吧?”
被她一语点破心思,朱秀云的脸一时红了。她恼林紫嫣的话说得过于直来直去,没个遮拦,常言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若是他回绝了,可如何是好?但是,她这么一说,自己的心思就像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这样也好。这时,一只灰颜色的鸽子扑棱棱落到窗台上咕噜噜地鸣叫着。朱小姐被它吓得一惊,随后又是一喜。鸽子、外国人、鸽会,在她的脑袋里联系到了一处。羞红稍褪,她轻啐道:“你个死丫头!胡说些什么。”接着随意道:“晚上,西区的迈克修也要去的,听说他是荣城鸽会的会长。” 丁一凡的心一动,刚才顾忌忽然不复存在。他想,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再看看墙上的自鸣钟说,“好了,可以起针了。多谢朱小姐的相邀,我定要去的。”起掉朱小姐头上的针,林紫烟吵着要回去。朱秀云起身时道:“七点钟,我把车来接你。”丁一凡点头送她们出了门。
返身回到屋里,李妈递上一杯茶。丁一凡揭起茶碗的盖子,轻轻吹了吹,将要喝,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大门哐当开了。那个早晨走了的荣三爷甩掉帽子一屁股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他一边哭嚎着一边数落着什么。丁一凡忙放下茶碗跨出门槛,见他出来,荣三爷上前扯了他的衣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的丁爷,你就行行好吧,离了我的白大鼻子我是没法活啦,快把它还给我吧……”
丁一凡连甩了几下,没有摔脱荣三爷的手,他恼恨地说:“刘看护,去找个巡捕!”刘看护和李妈一同上前拉开了荣三爷。就在这时,一个姑娘快步走进院子,她跨上一步扯了荣三爷的耳朵斥道:“稍不留神,你就出来生事,给我走!”荣三爷似很怕这姑娘,他歪转着头龇牙咧嘴地对丁一凡说:“丁爷,快救救我,快把那白大鼻子还了我罢。”
丁一凡细打量那姑娘,约莫十八九岁,高挑个子,挽了辫子在后面梳着一字横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刘海,一张圆圆的脸儿,穿了一身青布衣服,衬着手脸倒还白净。她见丁一凡瞅她,便道:“这位爷,巡捕就免了吧,舍弟疏于管教,请多包涵。”
丁一凡见到她那一刻就存了好感,见她说话干净利落,性格也豪爽,未免又多看了她几眼,笑道:“这位姑娘,方才原本是句气话,说说而已,不必当真的,荣三爷的鸽子确不在这里,假若进了我的鸽棚,必当奉还。”
那姑娘道声谢,提了荣三爷离去。丁一凡目送着他们出了门,看到几个与荣三爷一般大的少年呼啦散去。他望着两个转到街角的影子呆愣了许久,脑袋里又有好多疑惑,这女子不似大家闺秀,但她又称荣三爷为舍弟,荣三爷还相当的惧怕她,是何原由?从早上的情形看,荣三爷那帮子人一直都在他家的附近,难道他的鸽子真在自己的鸽棚?想到此处,丁一凡转头细看那阁楼,终是没有发现荣三爷的白大鼻子。
3
陆续又看了几个病人,已近中午。丁一凡换过衣裳提了食水来到鸽棚,将把粮食撒在地上,屋檐的缝隙里忽然窜出一只开花鼻子的白鸽。那家伙雄赳赳地落在地上,旁若无人地争抢着粮食,阳光的照射下,它脖子上的羽毛发着绿汪汪的光,尤其是那鼻子,核桃一般层层叠叠,犹如一朵绚丽的花。最可贵的是,这只鸽子的眼皮充满褶皱,几乎与鼻子连在一起。丁一凡不由赞了声,好一个尤物,实在是不可多得,怨不得荣三爷几次三番的讨要。那家伙吃饱后,围着盛水的瓦罐转来转去,根本不怕人。丁一凡把水倒入瓦罐,它一头攮进去狂饮一番,就去追逐一只漂亮的雌鸽,一点要离去的样子都没有。
丁一凡伸手抓那鸽子,那鸽子却是不躲不闪,反倒用翅膀奋力扑打着他的手。丁一凡觉着有趣,骂道:“你个霸道的家伙!”说罢,抓起它顺手扔到了外边。那家伙并没有飞回自己的家,只在天空中转了半圈,又落将下来,钻入鸽棚,继续追逐那只雌鸽。丁一凡连着扔了几次都如此,只得作罢。
吃过午饭,丁一凡用竹笼提了那鸽子上了大街,雇车到贝勒胡同。到了贝勒胡同的口上,就下车慢慢走进去,挨家看着门牌,到了胡同的最里边,他才看到一个门牌上写着“荣宅”两个字。
他咳了两声去拍打那门,里面传出声音:“红玉,有人来了,去瞧瞧。”又一个声音说: “还不是仕杰那帮子狐朋狗友,不定又寻他做些什么,早上差点捅了娄子,人家都准备叫巡捕了。”另一个声音说:“唉,你说这孩子,可如何是好呀?”随着话音,门开了一条缝,一个面色白净的妇人探出头道:“先生你找谁?”
丁一凡道:“这里可是荣宅?”
妇人见丁一凡衣着光华体贴,似新派人物,稍稍犹豫道:“是荣宅,不知先生找哪位?”丁一凡道:“我是给荣三爷送鸽子的。”
另一个声音道:“妈,你把门打开,是仕杰说的那位丁先生。”门打开后,早上的那位姑娘拿了块绣花布站在当院,她将绣花针别在一个花撑子上笑道:“先生请进来吧,舍弟出门了。”
丁一凡道:“那就不叨扰了,这是他的鸽子,钻到屋檐的缝隙里了,我没有看到。”
妇人摊开一只手说:“先生,里边来,红玉,快去沏茶,不要怠慢了客人。”
丁一凡见她热情,不好拂她好意,只得随她进来。越过粉壁,进了内院,两边游手抄廊,中间有一坍塌的假山,直抵上房。两株枣树,一株槐树,一方葡萄,由这里左右两转,是两所厢房。进得上房,十分的阴凉,原来院子里的那株槐树恰好遮挡了阳光。正面挂了一副山水画,看上去年代已经久远,颜色淡的地方有许多黑点,可能是苍蝇的粪便。地当中是一张红木桌子,旁边摆了一把红木椅子、两把藤椅和一个高腿凳。
妇人扯过一块抹布抹抹椅子说:“先生你坐。”丁一凡落座后,妇人寻了一包瓜子放到桌子上说:“先生在哪个衙门里做事呀?”丁一凡笑道:“你看我像衙门里的人?我是个医生。”妇人似不大相信,她摇着头道:“荣城的郎中我见过不少,先生不像,先生倒像一个洋学生。”丁一凡想起早上的疑惑,话随口出:“家里只你们几人?”妇人道:“强凑个家,还有一个老家人出城去收租子了。”
这时,那姑娘左手拿了一个茶壶,右手捏着两个样式不一的茶碗走进来。她将茶碗放到桌子上抿嘴笑道: “先生不要笑话,打得只剩下这两个了,不配套的。”说罢,她用手摁着茶壶的盖子,将水倒入碗里。茶水黑红,树枝样的茶叶梗在碗里打着旋儿。丁一凡眉头稍蹙,姑娘放下茶壶笑道:“用这样的茶招待您这样的客人确实不恭,丁先生还是将就着喝些吧,解渴的。”丁一凡的心思被她一语叫破,忙端了那碗喝了一大口。妇人站起身道:“先生你且坐坐,我去买些瓜果来。”丁一凡忙说:“不必麻烦了,我这就回去。”妇人道:“先生不忙走的,这些年来我们荣宅的人越来越少了,像先生这样的稀罕人更是经年不见,先生稍坐坐,我马上就回来。”
丁一凡只好坐了。姑娘转身出去拿了绣花撑子回来,坐在藤椅上低头绣着花。绣几针,便把拖着长线的针在头发上篦一下,然后让丁一凡喝茶吃瓜子。因无话,丁一凡扯过一个话头道:“刚才那大娘说强凑个家是何意?”姑娘道:“说来话长,刚才出去的是少爷的奶妈,以前是夫人陪嫁的丫鬟,我是护院武师的女儿,夫人临死前把少爷托付给奶妈和我的父亲,前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就成了一家子,我和少爷都称她为母亲,不再有主仆之分。”
丁一凡道:“那荣三爷似很怕你的。”
姑娘道:“我练过几天把式,他从小就是我带大的。再说,这个家里若是全由了他的性子,我们只好喝西北风了。”
说话间,大门哐当开了,一样东西被扔到了院子里。